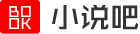今人称女性为先生(1)
既以读书与写作为爱好,便是选择了一种认真切实追求完美的生活方式,付出的是全部心血,收获的是一生快乐,就投入与产出而言,实在是百分之百的赢家。——扬之水
今人称女性为“先生”,多半是带着一种特别的敬意,比如“杨绛先生”。而在我心里,一直有个称呼是“扬之水先生”,但是当着她的面,听着她爽利的京腔,却说不出口,怕显得矫情,于是有时便以“赵老师”含糊过去。她的本名赵丽雅,联系着《读书》杂志的十载编辑生涯,当她越出知识界而为众多读者所知,已是精擅名物研究的扬之水先生。
棔柿楼,是扬之水先生的书斋名。东总布胡同一个矗立着西式小楼的院落,窗外的一株棔树,一株柿树,伴随着她漫长的读写时光。“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诗经》中这句话,她时时用以自勉。如今,《棔柿楼集》陆续出到十卷,她说,这套书是“全职读书十八年的一次自我总结”。
那些讲究反而是把自己束缚了
《棔柿楼集》是201 年、汪家明先生退休前、还在人民美术出版社任社长时启动的,立意要做成扬之水着作中“迄今最好”的版本。各卷多为相关主题的文章合集,涉及《诗经》名物、唐宋家具、敦煌艺术、古代绘画、焚香饮茶等方方面面以及古人生活中的各种大小物件,年代从先秦到明清不一,只有《桑奇三塔》出了国境,是国内第一部细密考察这一印度早期佛教艺术遗存的着作。另有《中国古代金银首饰》、《中国古代金银器》已列入计划,但扬之水先生说,还有许多增订工作未完成,出版尚需时日。
十本书摆在面前,从封面到内页,从内容到文字,都是极“雅”的。诗画中的舆服草木、花瓶中的一枝清采、焚香时的袅袅烟云、烹茶时缕缕清香,古人的日常所用之物,被时光的长河淘洗出异样的光彩,在今天被许多人艳羡追慕,“传统文化”似乎也终于有了一个踏实的落脚之处。于是,落笔皆风雅,成为许多读者对扬之水着作的第一印象。谈及此,她面露笑容:“大家看我的书,老是说古人穿的戴的有多漂亮,宋人生活多么优雅,实际上我的出发点根本不在这儿。”
她研究的出发点,自九十年代中期从国家博物馆的孙机先生问学,就已确立了。“我跟老师学习,最大的收获是他教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一开始他就和我说,文章一定要能发现和解决问题再写,否则就不用写。对我来说这是最低标准也是最高标准。上升到理论我做不到,我只能解决具体问题,一个东西叫什么名字,怎么用,它的始末源流是怎样的。我的文章都是这样的,发现了新问题,或者别人没说清楚的、说错了的,我才去写。”跟着问题走,为解决问题而做研究,决定了她的文章都有很强的内在针对性或开创性。比如她关于金银首饰的专题研究,“之前我老师写《明代的束发冠、 髻与头面》,是奠定基础的第一锹土,我还得在上面盖房子。我研究古代的香,也是因为没人谈这个,最初还有人不明白,问我是不是信佛。写茶,是因为觉得宋人煎茶和点茶的区别,还没有说清楚。我研究的出发点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个大伙儿好像没注意到。”
如果把扬之水先生想象成一个在棔柿楼中焚香品茗赏花的读书人,实属会错了意。见过她的人多半会察觉,她的衣着极为朴素,日常生活更是和“精致”、“风雅”不沾边。家里倒也不时有人送香、送花、送佛手,好意她自然是心领的,但是,“哪有时间拾掇这些啊”。一说这个她就笑了,“人家老问我写作时焚香吗?我哪有工夫焚香啊,喝茶也是沏一大杯子咕嘟咕嘟就进去了。那些讲究反而是把自己束缚了。”她永远觉得“没时间”,做研究“所有时间都投入也不够”,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她的生活就是读书、写作、到各地看展览,唯一的娱乐是“写大字”,一手娟丽的簪花小楷,人见人爱。
不过她确乎是“恋物”的。在一篇谈张爱玲的文章里,她说,“不过以我的‘物恋’之深,却无论如何造不出张爱玲那样的句子。大约一种物恋是用来丰富人生,另一种是打捞历史。”她读《金瓶梅》读《红楼梦》读诗词,总是被其中的各种物件吸引,这是天然的兴趣。她会把自己的“物恋”追溯到童年——攒手绢,攒糖纸,到东安市场买珠花,摆弄各种小物件。从四岁到十二岁,她和外公外婆生活,家境优越,外公的工资很高,外婆的生活很悠闲,想要什么都能得到,反而让她对物质享受不以为意。“那八年对我挺有影响的,享乐不过如此,足够了。”
童年时快乐富足的种子埋在她的性情里,恋物,却不求拥有,爱物,但不为物累。她过手无数文物,却无意收藏,她买书成瘾,但“一切只为使用的方便”,品赏把玩式的藏书,她说自己“永远不能及”。她也买过宝石,还给自己弄了一个“百宝箱”,“我研究首饰,就是想看看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另外也找找杜十娘的感觉。不是说一个东西我非要有,要是让我送人,那也没什么舍不得的。”
扬之水先生的幸福童年结束于“文革”爆发,之后她到北京房山插队,返城工作,换了几家单位,其中1986年至1996年在《读书》杂志的编辑生涯至关重要。她没能受到系统的学校教育,高考过了分数线,却阴错阳差没能上大学。她当然是自幼爱读书的,以曹雪芹为代表的古典系列,以浩然为代表的红色系列,是她阅读的底色,“后者的影响至于七十年代,前者的影响则恐怕是一生”。即使在没书读的年代里,她也有一本“随便翻开任何一页都有兴趣看下去的书”,那就是《新华字典》,她感激这本书让她在后来的日子里很少在读音上犯错。她说:“一般说我是初中程度,我实际上是高小毕业,四年级水平,五年级上半学期‘文革’就开始了,之后什么都没学。我们70届是最倒霉的,现在的学者里你去看,很少有70届的。”谈起“倒霉”的日子,她并无怨艾之情,她把自己的经历,视为一代人的共同命运。人所乐道的她返城后在王府井果品商店工作的“传奇”,她早就听腻了,觉得一代人都是如此,自己毫无特别之处。她说,无论什么样的经历,都是人生的财富。
但她毕竟是特别的。读书研学之人很多,但强烈的兴趣、惊人的勤奋、投入的状态和持之以恒的毅力,绝非人人具备。
九十年代中期,她受到《万历十五年》的启发,想依托《金瓶梅》里丰富的社会生活,写写“崇祯十六年”,结果“书里好多东西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她向王世襄先生请教,经王先生介绍拜入孙机先生门下。1996年,她调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学者之路正式开启。
未能专注的“文心文事”
扬之水研究的是“名物学”。这是先秦时代即已诞生、绵延不绝的传统学科,因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而渐趋式微。不过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意味着恰恰可以利用考古学成果为名物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沈从文先生第一个提出“名物新证”的概念,倡导结合文献和文物来研究古代名着。扬之水入门之初,孙机先生推荐的“名物新证”范本,即是沈从文有关《红楼梦》的一篇文章,通过考证妙玉的两只茶杯的名称与内涵,揭示出器物之暗喻和曹雪芹的文字机锋。她深为折服,并选择了“诗经名物新证”作为自己的第一个课题,这也恰是沈从文在六十年代初就提出过的。
在研究实践中,她关于“名物新证”的思路日益清晰:采纳考古学带来的新的认知与科学分析方法,“研究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有关的各种器物的名称和用途。它所要解决的第一是定名。第二是相知。”所谓“定名”,是指面对传世或出土的文物,依据各种古代文字和图像资料,确定其原有的名称;所谓“相知”,是指在定名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器物在当时的用途和功能。“定名”绝非易事。“你问我一件文物叫什么名字?我回答了,好像很简单。但是你不了解,我能知道它叫什么,包含了多少辛苦在里面。”扬之水先生说。
“定名”与“相知”,同时意味着对古代器物的溯源辨流,揭示其名称形制功用的演变过程。很自然,如果“名物新证”的视野进一步扩大,就会指向更为广阔的历史和社会生活。不过,除了贴近历史,扬之水先生始终念念于心的,还有文学。她的理想是:“用名物学建构一个新的叙事系统,此中包含着文学、历史、文物、考古等学科的打通,一面是在社会生活史的背景下对‘物’推源溯流,一面是抉发‘物’中折射出来的文心文事。”
从诗文中的“物”入手来理解文学,是她长久以来的心愿,《金瓶梅》、《红楼梦》、李商隐,都是她钟爱的题目。不过跟着问题走的研究方式,或许让她始终无法专注于此,写过一些专栏也都中断了。比如给《书城》杂志的一组“看图说话记”,是给“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的笺注挑错的,“笺注做得很好,但是一碰到诗词中的‘物’,很多都错了,或者是讲不出所以然。古人写的到底是什么东西?看看文物就知道了。”另外,她在《文史知识》上发表了几篇谈《金瓶梅》的文章,自己并不满意,“离我的期望值很远。我原来想这是我很心爱的一个题目,想写得能超越自己,但没做到。过去写金银首饰,已经把能写的材料用得差不多了,现在从文学角度写,还是有重复自己的地方。我不喜欢重复自己,想要超越自己又很难,所以就停下了。”
尽量避免重复,是她对自己的要求。“我愿意做别人没做的事,这还做不过来呢。永远有新的东西吸引我,我连自己都懒得重复,重复别人就更不愿意了。孙机先生老说我有洁癖,就连别人用过的材料,我都不愿意用,恨不得都是我第一个用才好——其实是避不开的,但我还是尽量自己发现点材料比较好。”
“就喜欢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这在情理之中,不过不知为什么,她不信任自己的文学感受力。“我觉得自己对诗的艺术性的感受力是比较差的,得努力去开掘。鉴赏诗词还得有理论修养,我对理论又不感兴趣。当年在《读书》的时候,黑格尔的《美学》等等,都通读了一遍,看完以后跟没看一样,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我对诗和小说里写到的东西就特别感兴趣,我想我还是扬长避短吧。”
其实扬之水先生有两本无关名物、非常“文学”的书。《诗经别裁》是在《诗经名物新证》完稿后,继续阐发《诗经》的文学意蕴。《先秦诗文史》则除《诗经》之外,还论及《尚书》、《左传》、诸子、《山海经》、《楚辞》等等,她称之为“读书笔记”。《先秦诗文史》自成一格,谈文学史很少有人提及,在她的着作中最不受关注,然而它的历史脉络清晰,对作品风格概括精当,每章也有严整统一的结构,吴小如先生评价说:“基本上做到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而有之。故‘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她一枝沉静的笔,贴着作品细细体味描摹其中暗藏的曲折,复以雅洁的文字道破奥妙:“《左传》用了预言来作成文字的魔方:从史的角度看,它是因和果,它是鉴戒与教训;从文的角度看,它是伏笔,它是叙事的前后呼应。”“《论语》多短章而总是气韵生动,《孟子》多长章而每有意趣,《荀子》在中心议题之下结构文辞,努力于图案式的整齐,珠玉之,黼黻之,灿灿然变化其文而决不出规矩,但重重叠叠间却终少奇致……”《先秦诗文史》的识见与文辞俱美,正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意。
莫辜负博物馆发展的时代
近些年,扬之水先生把大量时间交给了博物馆。2月份采访见面时,她刚从旅顺博物馆看完清代孙温的《红楼梦》图册回京,很快又要去长沙看外销银器展,接着还有成都、杭州……“一个月里就得跑两三趟。北京的展览更别说了,都得看。”她去了很多国家,都是直奔博物馆,“大英博物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都是守在旁边住了一星期,天天看。美国是从西到东,重要博物馆都去了,听说有个大峡谷,根本没见过。”
“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现在中国的博物馆事业这么好,免费,而且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拍照。国外就不是这样。”扬之水由衷地说,“博物馆给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便利,能看到东西,一下就明白了。清代学者做过那么多考证,但是见不到实物,画出图来就不是那么回事,要不他们能解决多少问题啊!”
她给文物定名,反过来也服务于博物馆。文博界对她的研究越来越重视,有的展览直接摘引她书中的内容,作为展品说明。她还会给博物馆提建议,“现在大家办展览,比较重视历史线索,对文学还没注意到呢。我就建议用古诗词里提到的文物做展览,这样老师也可以领着学生去看,古诗词里看不懂的,去博物馆看看不就行了嘛。”
扬之水先生说,她逛博物馆看的不是“展览”,而是“东西”。她直奔近期研究的题目,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其他文物挨个拍照,留作资料。比如,去年她看的展品以明清为主,为的是撰写“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大系”里的“杂项”卷。从去年年底到春节期间,她停止一切活动,包括唯一的娱乐“写大字”,“所有的材料都在手边,一个多月写了四万六千字”,终于要收尾了。
然而她手头的工作永远做不完。“杂项”弄完了,她打算继续通读《汉语大词典》,完成配图工作。《汉语大词典》修订,原本是请她审读图片,但是她觉得原来的配图不行,最终是自己从头来。“我想先把这个弄完,再去写金银器。”另外,她还打算和一位编辑合作,为2018年的《每日读诗》日历配上文物图片。
为什么扬之水先生会接下这些琐细的配图工作?都是为了新的“名物辞典”。她说:“做一部辞典太难了,我想以我一人之力,一辈子也做不出来,现在可以用我看到的东西,研究的成果,先打个基础。将来有这么一部辞典,大家就能够方便地查阅,还可以利用新材料,不断地修订刷新。”
一套含蓄妥帖的书
读书、写作、看文物,从不衰减的热情和勤奋,却仿佛披了一件沉静的外衣,一如这套《棔柿楼集》。“迄今最好”版本的目标,也是由内而外,从内容到装帧的全面追求。责任编辑王铁英女士说,扬之水是一位“负责、较真又体贴”的作者。她修订整理了所有文字,并核校文献、补充新材料,甚至根据新材料重写。出版过程中若有改动,她常常算好字数和位置,一一标在样稿上,尽量减少重新排版的工作。如果编辑发现了某个错字或某处疏漏,她会“高兴得不得了”。
《棔柿楼集》由宁成春先生和人美社的鲁明静负责设计,他们和汪家明、王铁英一起琢磨确立了整套书的设计思路。“最初我们也尝试过图文混排。但是汪老师提出了‘图不害文、文不害图’的原则,要求文章不被图片割裂,图片能充分展示书中的器物纹样,同时图文搭配,相互参照。最终我们确立了网格排版的设计方针,这就像建立一个王国,制定了法典。”鲁明静说。《棔柿楼集》做得很漂亮,从封面到浅灰色环衬、带有灰色图案的前页、扉页、目次页逐渐过渡,内页印刷正文是90%黑,注释是80%黑,全书形成黑白灰的节奏关系。封面图案微微压凹,貌似采用了古书的插图,其实是宁成春先生手绘的,书名也是他参照明刻本手写的。每卷的最后,都有一幅小小的拉页,多为扬之水先生精美的小楷手迹,是“给读者的礼物”。《棔柿楼集》从里到外在细节上见功夫,“想给人的感觉是,它就在那儿。”鲁明静说。一套细致妥帖,内蕴精华的书,想来也是和作者的研究路径、文字气质相得益彰的。
和扬之水先生见面的时候,东总布胡同的小院还残留着冬的萧索,如今春和景明,花朵树木和邻居们种的蔬菜,又将给这个高楼大厦包围中的“孤岛”带来缕缕生机。院落中那棵棔树,已经走到它的岁月尽头,不能再点染夏日的宁静,然而那粉红色的花的精魂,仍将和“棔柿楼”一起,照拂着主人的寸寸光阴。简单生活,专心治学,一切都是那么充实明朗。
插图选自《棔柿楼集》
(编辑:王怡婷)
南宁白癜风医院海口治疗白癜风费用陕西妇科医院哪家好- 下一页:六月安然(1)
- 上一页:九霄武帝第1980章狂龙爆碎
- 06月21日都市给狗狗戴脖圈和牵引带好吗图位置
- 06月21日都市给猫咪清洁牙齿耳朵眼睛的办法位置
- 06月21日都市夏季饲养柯基犬要特别注意的五件事位置
- 06月21日都市夏季饲养喜乐蒂犬如何为狗狗保持干净的卫生位置
- 06月21日都市给猫咪喂食肉类蛋类和鱼类须知的一些注意点位置
- 06月20日都市猎狐犬异嗜癖的矫正位置
- 06月20日都市猎狐梗幼犬冬季的养护位置
- 06月20日都市猫不正常脱毛的原因有哪些位置
- 06月20日都市猫咪不吃猫粮应对方法位置
- 06月20日都市猫咪一直抓沙发怎么办位置
- 06月19日都市狗狗断尾的原因你知道吗位置
- 06月19日都市狗狗排尿频繁的原因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