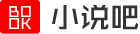流云讲纱厂话的人散文
摘要:一间百年老厂不复存在了,曾经的辉煌,曾经的岁月却依然记忆犹新。那间厂,那些讲一口纱厂话的父老乡亲...... “纱厂话”其实是一种方言。
方言本该以地域名称来命名的。在湘西雪峰山下沅水河畔黔阳县一个叫作“安江”的镇子里,除了原住民的安江话以外,一多半的人却操一口与当地语音不同的发音。只因为他们都是同一间纱厂的工人或者家属,那一口好听易懂的语言就被当地人称作了“纱厂话”。
在镇子里,能够说一口纱厂话的人曾经感到过骄傲。因为他们工作的那间工厂,被称作湖南第一纺织厂。不但是“第一”,前面还加了响当当的“国营”两个字。国营第一的工厂里当个工人,在当年那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走起路来昂首挺胸的,那份神气劲,人见人眼红。
工厂上世纪初1912年建在省城长沙,原本为官商合办的经华纱厂。第二年收归了省办,到19 2年时,员工巳增加到了 000余人。年产纱两万五千件,棉布两千余匹,年盈利数十万元。19 8年9月,小日本入侵湖南,省政府即下令该厂将一万纱绽,两百多台布机等生产设备随同工人,迁到了偏远山区的黔阳县安江镇。
纱厂迁入,让不足万人的小镇涌进了数千的“工人阶级”,拖儿带女的外来人口数量一下子超过了镇子里原有居民。圈地建厂的地盘也占据了镇里半壁江山。昔日冷冷清清的街面上热闹起来,为数不多的商铺变得门庭若市,进进出出的买主,大多是每月有些工资进账的纱厂工人。他们从省城长沙迁来,让生意红火,给小镇带来生机,山区的老百姓对他们也就变得十分恭敬。乡下人那时节对工人阶级这个称呼还不太怎么适应,私下里也只称呼他们为“纱厂佬”。
从省城迁来的纱厂佬讲话像极了长沙口音,仔细听听却又听不出城里人的那丝丝傲气。入乡随俗了,却也没有山区人言语中隐隐地那股蛮劲。他们与人交流显得彬彬有礼,说起话来又十分好听。全镇子老百姓对这些讲纱厂话的人十分友好。
安江是县治所在,解放后不久,地委和行署也都迁到了这里。按说这山旮旯交通并不方便,县城里原有那几个手工作坊也与工业二字根本沾不上边边。因为纱厂迁入,沅水河里为工厂运棉花运煤的船来来往往多了,翻越雪峰山公路的汽车也川留不息了。纱厂成为方圆几百里范围内工业的品牌。国家既然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那么党政首脑机关落户安江也就顺理成章。
政府官员对这些讲纱厂话的人情有独钟,工厂经营中的种种问题都是上级必须关注支持的大事。当年一条规矩是凡地区一级召开的会议,不管主题是什么,组织参会人员到纱厂生产车间参观成了铁定的议程。车间里从棉花棉纱到棉布,生产环节环环紧扣。工人只要一进入岗位就穿梭不停地忙碌,哪道工序稍一停摆,上下环节均受影响。组织参观的目的,就是要让各行各业人们学习纱厂工人讲规矩守纪律的好作风,在老百姓心中树立起工人老大哥的形象。
讲纱厂话的女人是这个镇里最靓丽的风景,这是被公认了的。那时候的人相对保守,前突后翘的女子走在大庭广众的眼皮底下会被认为有伤风化。而只有在流水线上工作的纺织女工,因为车间温度高而穿着单薄,工作围裙紧裹着那曼妙的身段十分亮眼。加上在机器间逡巡的那一整套操作,日复一日地演练,早就被编排成轻盈的舞姿一般,以至于外人只要听说到纱厂参观就会眉飞色舞。很长一个时期,机关干部,解放军军官,还有那些喝墨水多的老师们找对象,都乐意找个讲纱厂话的女人。每周末的舞会上,除纱厂话以外那些喷一口南腔北调的男人全都是厂外来客。虽然有所企图,厂区门卫也并不加以阻拦。小镇依山傍水,山青水秀空气都带些甜味,本地女子一个个出落的桃红花色韵味十足,但在这些说纱厂话的女工面前竟没有了竞争优势。“纱婆子”的称呼从她们口中出来,酸溜溜那股子嫉妒之情毫不掩饰。
讲纱厂话的男人疼老婆,爱家人,吃苦耐劳有担当。那个年代没有什么计划生育,一家三五个孩子的现象极为普遍,七八张嘴要满足并不容易。男人们在纱厂干那些捋棉条接线头的活免为其难,他们大都从事卖体力的辅工。为了这个家,休息日或倒班之时,他们会上十几里以外的山里砍柴。还有的在郊区的荒山上开荒种菜,真正的亦工亦农。
讲纱厂话的人性情开朗热爱生活。厂里子弟学校,职工夜大,医院疗养院,文化宫俱乐部一应俱全。周末电影场场满座,厂里篮球队在地区比赛常拿冠军;京剧团锣鼓一响,直把个老戏迷们癫得摇头晃脑如醉如痴;管乐团白礼服一亮相立马会引起围观,文工团几十年间人进人出却长盛不衰。节目演到了省城,还演到了北京怀仁堂。甚至在纱厂破产改制二十年后的某天,已八十高龄的老文工团长一声吆喝,前后几代百十口人立马从山南海北齐聚一堂。这群徐娘半老甚至年愈古稀的老文艺在小区球场搭台表演时,诺大个讲纱厂话的地盘万人空巷。
讲纱厂话的人通情达礼还十分执着。破产下岗让他们为改革开放付出了牺牲,稍作调整后便重新开始全新的生活。有的自主创业,有的外出谋生,日子过得有滋有润。老家里留守老人占了绝对多数,可就这些七老八十的人仍不忘初心。曾经的某个冬日,相邻几栋家属楼十几位老人端个小板凳围坐在一起晒太阳,一位老者在读报纸。旁边墙上贴着的红纸上写着家属区几栋至几栋老党员“党费缴纳登记”。交费金额各不相等,全靠自愿。原来他们把凑齐的党费集中购买报刊和学习资料,定期在过他们的“组织生活”。此情此景,让路人无不动容,对这些老党员们肃然起敬。
如今,让这群讲纱厂话的人凝聚在一块的纱厂不复存在,可纱厂话作为一种情愫依然相传。孙子辈在外地尽管京腔嘎嘎,只要一踏入家乡这片土地,便自然而然说起了纱厂话。走到天涯海角,只要听到这种熟悉的乡音,稍作寒暄之后,那种他乡遇故知的亲情便油然而生。
纱厂话,在这些人的心中已然成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子子孙孙,代代传承,不离不弃。
我愿为这些讲纱厂话的人们祈祷、祝福!
共 2257 字 1 页 转到页 【编者按】在湘西雪峰山下沅水河畔黔阳县一个叫作“安江”的镇子里,除了原住民的安江话以外,一多半的人却操一口与当地语音不同的发音。只因为他们都是同一间纱厂的工人或者家属,那一口好听易懂的语言就被当地人称作了“纱厂话”。工厂上世纪初建在省城长沙,19 8年9月,小日本入侵湖南,省政府即下令该厂迁到安江镇。从省城迁来的讲“纱厂话”的工人阶级很快融入当地,与老百姓十分友好。讲纱厂话的女人是这个镇里最靓丽的风景,讲纱厂话的男人疼老婆,爱家人,吃苦耐劳有担当。讲纱厂话的人性情开朗热爱生活,通情达礼还十分执着。作者用细致的笔墨回忆了那个特定时代的一段历史,一代纱厂人的生活。如今,纱厂不复存在,可纱厂话作为一种情愫依然相传。只要听到这种亲切的乡音,他乡遇故知的亲情便油然而生。感谢作者将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缅怀它。【:莫道不销魂】
1楼文友: -05 16:57: 0 感谢老伯用文字将过去难忘的人和事记录下来,您也曾在纱厂工作吗? 用点滴文字,守候心灵家园。
回复1楼文友: -05 18: 1:19 谢老师快速放行!我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那间厂工作了八年。
2楼文友: -05 18:29:02 为老师快速回应点赞!老头敬礼了!
楼文友: -05 19: 2:14 不用谢,老伯,下午有时间正好看到了。应该把生活经历记下来,期待您的更多作品。 用点滴文字,守候心灵家园。
4楼文友: -06 22:1 : 7 看了这篇文章我很激动,我爸爸我妈妈我爷爷奶奶都是在纱厂工作奋斗了一辈子退休的,我是安纺子弟幼儿园,安纺子弟小学毕业的,可是这充满回忆的地方已经变成居民小区了。说起这个学校,也只有纱厂人知道了。幼儿园也已经是现代化幼儿园,改名成安江幼儿园了。就连纱厂的子弟中学也变成洪江市第六中学了,现在也只剩一栋教学楼了。旁边都是现代化教学楼。小时候妈妈下早班都会给我在食堂买个豆沙面包回来吃,会带我去纱厂里面坐 碰碰车 去八角亭玩,到篮球场看打篮球比赛。还去厂里的礼堂里看节目,记忆犹新的还是爸爸参加的大合唱,妈妈有空晚上带我去工房里找同事玩,有男工房和女工房之分。逢年过节都会发很多东西。小时候盖的被子用的盆子和杯子都有纱厂的标签。那时候还有纱厂电视台,每天晚上都会播好看的电视剧,我还会每天看半个小时的纱厂。纱厂很大覆盖面很广,小时候去同学家也住的很远,有新八十户老八十户新工房还有什么四十五户等等,小学放学排路队回家,都是站两排一排是后卫门一排是前卫门。那时候每次放学回家在路上就会遇到好多骑单车走路的叔叔阿姨出来,现在真的是很怀念那样的画面。
回复4楼文友: -07 22:16:0 你也是讲纱厂话的人了,握手。我敢说你爷爷奶奶我也许认识,因为我早就爷爷级了
5楼文友: -09 22:50: 6 短短几天,这篇散文阅读量接近9000,是被朋友转发后在此文中纱厂群中广为转发.我为讲纱厂话的人们点赞!该厂人才济济,希望大家投稿江山流云,祝福朋友!
孕期缺钙喝什么汤好
孕妇小腿抽筋怎么按摩
怀孕左侧腰疼什么原因
优卡丹小儿氨酚烷胺颗粒怎么吃痔疮栓哪个好使
宝宝口臭
- 下一页:柳岸村里的编筐者散文
- 上一页:母亲做的鞋有样
- 06月21日科幻给狗狗掏耳朵需要注意的五件事位置
- 06月21日科幻给猫咪补充蛋白质有什么好处位置
- 06月21日科幻夏季饲养比熊犬攻略防虫驱虫抗过敏位置
- 06月21日科幻夏季饲养巴哥犬狗狗健康最重要位置
- 06月21日科幻给猫咪手术麻醉的程序及注意事项位置
- 06月20日科幻猎狐犬患皮肤病怎么办猎狐犬常见皮肤病的相位置
- 06月20日科幻猎狐梗犬中暑的预防与救治位置
- 06月20日科幻猫与狗常见五大牙齿问题位置
- 06月20日科幻猫一天要睡多久睡的时间比较长位置
- 06月20日科幻猫咪一胎能生几只小猫呀一般在只之间位置
- 06月19日科幻狗狗无缘无故吠叫之解决对策位置
- 06月19日科幻狗狗摇尾巴的频率代表兴奋程度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