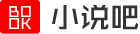p1pp那一年我第一次没有和父母一起过春
1
那一年我第一次没有和父母一起过春节。就像春节放假前我对公司行政负责收集员工订票信息的小陈说的, 是的,我去 他们家,你没看错。
她晃着新烫的头,像所有面对新人的老员工一样,表情严肃、义正辞严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你看,这跟你报道时登记的父母所在地不一样。
我相信,她也许是对的。公司不是票贩子,不会你随便填上一个地名就慷慨给你一张春节前的火车票,何况我还需要两张票。尽管代订春运火车票是这家公司多年的员工福利,他们有这样的渠道,但太随便的东西便不珍贵了。这道理所有人都知道。
我站在她的办公桌前,想了想,才终于没有说出本来已经想好的话 不过是河北一个县城,去那里的车票当然会比我父母所在的遥远南方更容易搞到。所以,我以为自己是在给公司减轻负担。只是我好像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是不是我那时应该去惦记的事情?
他想去火车站排队买票。听他说起来,好像也不太难。他说,每年春节,他都是这么干的。他们一起排队买票的有很多人。吵吵嚷嚷、神采飞扬, 让我想起当年我们也是这样一起去美国使馆示威的。 他说的是大学时候的事情。一些年轻人为北约轰炸使馆的事情激动,于是约好在当天晚上把临时写好的标语和旗子卷起来、塞进书包,从中关村连夜走到了朝阳区的美国大使馆。刚到那里,就看见警察拉起两条长长的荧光色带子,命令他们解散。他们很配合,说是非暴力不合作。这样又结队走回中关村。天已大亮。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有他们一起参加游行示威的伙伴们,在学校论坛上终于有了有意思的谈资。他实在不想成天谈论食堂的涨价和游泳馆的美女了。他那时已经大四,整整四年,他都只能无聊地跟学校所有无聊的人一样,假装很关心食堂和游泳馆的事情。
他始终觉得,会有重要的奇迹发生在自己身上,而那也并不需要他特别做些什么。我想,他一生都会这么想。
他说,大概买票也不过就是这么回事。只要享受这个过程,其实没那么痛苦。 毕竟, 他又补充着, 去虎城的火车那么多,春运期间还有加班车、临客,我总能买到票的。
我为什么要自告奋勇把买火车票的事情包揽下来?事到如今我仍不太明白。
大概是我想强调一下自己已经工作的客观事实,炫耀一下那家公司唯一的员工福利⋯⋯也或许,他根本就是在等着我说出这样的话。那段时间,他会说夜里多么冷, 这是百年不遇的寒冬 。
事实上,被他说中了。那一年的南方,像更年期妇女错乱的生理期,冰雪霜冻都开始任性,终于成为灾害。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在多年不见雨雪的南方山城,发短信告诉我说, 竟然有人被冻死。 他们不敢给我打电话,因为那个春节我在 他们家 。父母不确定我在 他们家 是否待得自在。他们不希望我因为一个突然的来电而陷入某种尴尬处境。他们都是十二分的老实人,平生最痛恨的事情是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烦恼。所以,他们一生都在忙于让自己尽可能隐形,以至于我那一年都几乎很少想起他们。况且,我那时在虎城 一座曾经有工厂如今落寞了的北方县城。虎城有暖气,这让我无法理解那种会冻死人的南方的寒冷到底有多冷。我已经在北京上了四年大学,又在北京工作,与南方冬天有关的记忆,已经很淡。
我只能把那座河北县城的名字,虎城,含糊叫作他们家。我告诉小陈、告诉部门领导、告诉所有问我的同事, 我去他们家过年。 我一边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像是轻描淡写,仿佛这不是什么大事,一边又暗自希望小陈和他们都能够迅速理解 他们家 是我男朋友家,然后,就不要再问下去了。
我当然也可以把那里说成是 男朋友家 。但那未免太张扬了些。我只有二十二岁,还不认为男朋友三个字是可以拿出来让小陈这样的同事咀嚼的。公司里有很多单身,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情。但我在进入公司第一年便领悟到不要在男朋友的事情上有任何炫耀 尽管他其实没什么让我炫耀的 那是在所有事情上都不该炫耀的年龄,除了年龄本身。
公司给了我两张去虎城的慢车卧铺票,于是我欠下小陈很大一个人情,以至于后来从那家公司辞职离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依然没有还清。在这一点上我大概遗传了我的父母,认为所有麻烦别人的事情,到最后都不过是让自己痛苦。
2
火车不能直接到虎城,我们还需要坐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火车到站前,我去车厢连接处的卫生间门外,摇摇晃晃排队,在拿着牙刷毛巾等待洗漱的人中间,抢占一小块落脚之地。我对着卫生间满是水渍的镜子给自己鼓气,以便应付接下来的七天。我抓了抓自己的卷发,希望一夜的辗转难眠后,它们依然可以保持出发时那种蓬松好看的样子。我也许需要一点干净的水,用来激活头发上那些隔夜的发蜡。但在一辆春节前的火车上,我明白一切只能从简。我可能是从那时开始感到,这件事并不会像我预感的那么好。因为火车还没有到站,我已经感到沮丧 不只是因为我无法让头发处于一种最好的状态。它们软趴趴贴着头皮的样子,很不幸,将是我留给他父母的第一印象。
北方的冬天,像加上单色滤镜后的照片。只需要盯着那单色照片看一会儿,你肯定昏昏欲睡。我觉得自己睡了漫长的一觉,默默感激在这辆慌慌张张的公共汽车上,还可以占住一个靠窗的座位。除夕这天还在路上的所有人,都会慌张,也许他们才对横冲直撞的公共汽车保持住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沉默。
他坐在我旁边,蓬松的外套像棉球,让我与这个世界阻隔开。公路干干净净,行道树只剩下干枯的枝条,把一切都分割得支离破碎 那些收割之后的田野,再也不被重视。除非天气转暖,种子可以在化开的冻土中扎根。我大概睡了很久。因为在通宵的火车上我始终无法入睡。我告诉他,卧铺车厢里靠窗的枕头太低,低到我担心自己稍不注意就会被甩出窗外。他在下铺开心地笑,心情极好地认为我不过说了一句有些幽默的话,所以他就这样忽视了我真正的困扰。
出发前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被这种幸福的情绪笼罩着。我判断不出他这掩饰不住的幸福,是否是因为我?因为他似乎并未在电话中对他的父母过多说起这件事。他即将带一个姑娘回家过春节 在他看来,这样便足够表达这件事所有的象征性。我本来以为,那会是被浓墨重彩渲染的许多细节,就像我从北京火车站便开始拍下的照片一样。我隆重记录着沿途的景象。
那时我不能想太多。在陌生的县城陌生的家庭,他是我唯一认识并信赖的。我潜意识里希望自己尽量去迎合他,就像我迎合着公司里的每个人一样。
当我在公共汽车上醒来的时候,才发现这只是一次短暂的睡眠,因为窗外的景致看起来原封未动 回程的时候我明白,哪怕公共汽车在这条没有弯道的路上永远走下去,它们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北方平原地带的冬日乡村,并不需要变化。它们只需要安稳保持住同一种单调,才能让人们对来年的春天怀抱希望。
那年冬天很奇怪,南北方之间的交通变成一件困难的事。因为南方的冰冻。快递停运,我在网上购买的礼物无法送到北京。临行前我们两手空空地在前门仓促买下两只真空包装的烤鸭,像很傻的游客一样,询问那是否和全聚德吃起来一样?我的父母寄往北京的那些南方的年货,也滞留在途中某个货仓。那些腊肉、火腿、冬笋,在来年春天终于抵达北京的时候,看起来已经毫无生气,像是被遗弃的什么古怪动物的尸体 我本来希望可以自己做出腌笃鲜来,以此显示南方的骄傲。它们后来成为南方的耻辱 我无法在北京的厨房让它们变得美味。生活中许多美好的愿望,便这样因为错过了恰当的季节,变成让我无法面对的现实。
幸好今年你不用回南方。 他看着公共汽车上的小电视里南方冰冻灾害的新闻,这样说。我想,这大概是他身为北方人的骄傲了。只是睡眠不足的我,觉得这句话听起来充满了冒犯,而不是像他的本意那样,只是想表达对我的某种安慰,或许还有和我一起回家的快乐。
我没有说话,沉默地犹豫着要不要从安全带勒紧的斜挎包里掏出相机。那可能会很费劲。我也很快让自己放弃了这想法,因为这始终如一的景色让拍照成为一件夸张的事情。
我们从未一起旅行过。这是第一次。我们都有所期待,北京让我们喜爱又无奈。如果既能离开北京,又不会影响我们所眷恋的那些东西的话,无论如何也是不错的事情。旅行听起来足够浪漫,所以也是奢侈的事情。所有浪漫都是奢侈的,那时候我们在这一点上已有共识。
他滔滔不绝地谈起电视台最近一期栏目的时候 那是他的工作,被聘任的电视台摄像,另一种说法是临时工 我觉得世界很宽阔。二手车市场的黑幕、小学择校生的后台、物业公司暗箱操作的猫腻、儿童自闭症的救赎、农民工的讨薪⋯⋯他把镜头对准他们,让所有人在电视上都能看见他在镜头里看见的景象,像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大概他用镜头记录的那些现实太不堪,于是他相信浪漫于这个世界无益,对我也是如此, 北京给所有人机会,你只是要做好准备。 他擅长讲这种鼓舞人心的话。这大概是我喜欢他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些暗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在一个所有人都把你当打杂小妹的公司坚持下去。我认为自己的管理专业,应该呈现出一种掌控局面的优越。事实上我只是被所有局面掌控着。也许以后我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管理者,像电影里所有的女强人一样,在每天早上踩着高跟鞋、握着星巴克的纸杯走过公司走廊的那段距离里,便解决了无数等待我去解决的问题。这画面太遥远,我需要他的暗示,才能让自己相信那也许真的会实现。
他的父母并不能理解这变化越来越快的世界上,竟然还专门有一门专业叫做管理学。他母亲在大厨房里两只大塑料盆中间端坐,一边择菜一边念叨着 管理、管理 。她不是一个太精明的女人,因为她在做事的时候,便无法专心聊天,所以她口口声声说着管理的时候,其实心里肯定还是想着手里的韭菜。我从来不吃韭菜,我没有说。我只是尴尬地笑着,让她以为我已经认同了她刚刚停下手中的活计表达出的看法, 管理?管理管什么的?是管人?还是管什么东西? 我突然觉得自己的专业是一个很难解释的事情,尽管在刚刚过去的写毕业论文一年里,我觉得自己对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有任何困惑。我说, 这不太好解释。 那语气听起来,很像是想要蒙混一些什么东西。我于是也去择韭菜。她说那是做饺子用的,听起来她对此很满意,对韭菜饺子充满期待,又像是在讨好我,因为她准备了这么多韭菜。我暗自希望她还准备了其他馅料,随便什么都行,不一定是我喜欢的荠菜。北方会有荠菜么?那时,我已经无法集中注意力了。因为他们家人开始热闹地说话,用虎城方言。我听不懂他们的话。这让我惊讶 难道不是只有南方的方言才会奇怪得像日语么?在北方县城,我第一次遭遇到语言不通的局面。在那之前,我相信所有北方人都讲着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他说,这是虎城方言,因为县城太小,其实也是一种乡土语言。他后来还讲过虎城方言和宋代、客家甚至成吉思汗的关系,我想他只是想表示对家乡的偏袒。我不在乎虎城和成吉思汗的关系。
他的父亲看来更难应付,因为他问, 学管理的人应该考虑问题很 复杂吧? 我尽量不让自己以为他是在暗示我的心机。所以,我费力地想用 科学管理 或者 数据库 之类的东西,来回答他的问题。但我很快发现这并不容易。他是商人,尽管只经营着一家小超市,但也足够让他具备商人的精明。他用小超市的经营做比方,解释说其实管理更像是与生俱来的天赋,比如他自己。而不是一门学问,他说, 他妈妈就绝对管不好超市。 这是他们家的现状,父亲精明有权威,母亲简单顺从但木讷。
你和他们聊得不错。 他后来这样说。我希望他从没这样说过。
虎城和南方县城不一样。在我快要以为虎城已经大到没有边际的时候,我到达了它真正的边际,他们家。几栋楼站得很整齐,像是规则的多米诺骨牌。这里的一切都是规则的,都是方形的。道路、楼房、整座城、小区、楼梯,还有他们家,客厅旁边两个规则的卧室,从卧室走出去,是规则的方形阳台,客厅另一端,是大厨房和卫生间。所有家具也是方正的,像他父亲的国字脸,面目严肃。
我们四个人,是这套大而空荡的两居室里,唯一不够方正的东西,于是很有些格格不入。站在阳台上,可以看见真正空旷的土地,看不出会作何用途,没有耕种、没有修建、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只是纯粹的土地⋯⋯世界的尽头是不是就是这样?
这都是他在向我介绍这里布局的时候,我想到的东西。他希望我在这里的生活,可以自在方便。我想我大概忽略了他强调的这里一百四十平米的使用面积。
一年中多数时候,他都和我挤在不到四十平米的出租房里。我们认为所有东西的最大用途只是 占地方 ,所以我不得不放弃此前对共同生活的许多期待,咖啡机、茶盘、浴缸、大衣柜和网球拍,都必须为此作出牺牲。
后来的几天里,我随他去亲戚家拜年,惊讶地发现这里所有家庭都住在格局几乎一模一样的房子里。他们认为这是不错的事情。
这其实都不是重要的事,尽管它们已经足够让我不适。但我没有太多选择。不过是一个节日。
在这里,我不会看到他的成长痕迹。这是他们刚刚入住的新房。他其实和我一样,对这里也是陌生的。我们都是这里的新人。他把我们的牙刷插在洗脸台上的杯子里,那像是同样不知所措的两个入侵者,带着不一样的情绪与愿望,忐忑地依偎在同一个漱口杯里。我想他也并不比我更容易。他需同时照顾我和父母的情绪。他大概也感到,其中有些不太容易应付的事情,或许这跟他出发前的想象不太一样。
最初见面的喜悦渐渐平息,所有人都明白彼此将在几日里共处一室的现实。他的父母表示很盼望这天,就像我们也曾经很盼望这天一样。但它真正到来的时候,呈现的面目不是空洞的喜悦,而是牙刷、韭菜和艰难的对话,或者别的一些什么东西。
直到这一刻,我想我还可以应对。直到我看见他的父亲在脱裤子。
只有我真正惊讶。客厅里,我们坐在沙发上,他的母亲在厨房,准备着在我看来永远也不可能吃完的饺子。我忐忑地希望不要出现难堪的沉默,希望他可以为我遮挡很多不必要的问话,就像在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一年里他无数次做的那样,让我相信无论发生什么难题,他都可以让我免受伤害。
大概是真没有什么话题可以让我们共同参与了 我们已经这样坐着,进行了大半天的交谈,期间吃过两次韭菜馅的饺子,跟午饭晚饭都没有关系,他们只是会突然觉得饿,于是煮一锅饺子 他的父亲,从沙发上慢悠悠站起来,开始解皮带。
我很惊讶,但还可以让自己极力镇定,我不会往他父亲的那个方向看。我想那或许真的太难了,以至于我都没有留意到他们的神情都没什么变化。
他的父亲已经把裤子脱掉了。当然,只是外面的裤子。他穿着一条看起来很厚实的深蓝色棉裤,裤裆的地方两颗显眼的白扣子,像两只黑暗中的眼睛。
他这样站着,两手背起来,略弯腰,解释说, 暖气实在是太热,在屋里这样舒服些。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对我说的,于是我看着另一个方向,含混地点头。我希望他不要再说下去了。我认为自己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幕,毕竟除男朋友外,没有一个男人在我面前脱裤子 哪怕他其实仍穿着严实的棉裤。
我斟酌着这是否是对我的无视?或者故意的蔑视?这让我感到自己快要无法坚持下去,在一张方正的木沙发上。我的头发还贴着头皮,因为他说 除夕这天不要洗头洗澡,那不吉利。 一切都像我的头发,看起来糟透了。
他的父亲又坐回沙发上,该是想继续这半天的谈话。他们父子已经一年没有见面,想来该有无数的话在等着倾诉 至少我和父母见面的时候,总是这样。
但他们只是沉默,像是共同发现了我的紧张。这似乎成为他们继续交谈的障碍。
他搂着我,轻轻拍着我的肩,仿佛想要安慰我。但我知道,那没什么用。
何况,他随即也跟他的父亲一样,脱掉了自己的牛仔裤,像是在做任何一件平常的事情一样。他只穿着贴身的棕色棉裤,还是坐在我身边。
今年的暖气特别热,是吗? 他说。
他的父亲很高兴地说, 新房的暖气就是比老房好,我专门多装了几片暖气。
他的母亲在厨房接话,用方言说着什么,从我零星听懂的几个词判断,她大概在说她的丈夫实在是有远见的一个人。
他没有再楼我,尽管他贴身的棉裤已经勾勒出了我再熟悉不过的腿部肌肉的清晰轮廓。如果在北京,在我们不到四十平米的房间,我会想去抚摸那有力的曲线,或者依偎着它 那更像是我的海防线,我依赖着它,抵御着每一个寒意深重的夜晚。我们在北京的房间,没有市政供暖,只有电暖。我们谨慎地使用着电暖这种更有南方色彩的东西。每天回家后打开,穿着厚重的外套等它慢慢变热。睡觉前,我们会把电暖关掉,因为它让我们不得不考虑电费的数目。我总是可以熟练地掖紧被子的每丝缝隙,在南方人们都这么干。我也会让自己的身体尽可能紧贴他,以为这样,便会足够温暖。
4
他说要带我出去逛逛。其实是坐出租车去的。小时候我总是垂头丧气地跟父母去散步,仿佛不需要特别注意就走完了县城所有的路。现在,我们坐车穿过北方县城,沿途我看不见太多人或车辆。春节是冷清的节日,在那些一模一样的房子,才可能会有一模一样的热闹。
虎城曾经繁华过,依靠生产化工产品。多年前,有很多外地人搬来,把县城撑大了。人们在膨大的气泡上安家落户,急于让这里看起来跟远方的家园没什么区别。来自四面八方的土特产和口音在这里进行过一场盛大聚会。
没有不散的宴席。他说。
后来工厂关闭,因为规模不够,无法进入更重要的序列获得继续营运的保障,成为终究破灭的泡沫。曾把这里当作家园的人,很快急匆匆散去,像过境的昆虫为生存风风火火,留下一些空荡荡相似的房子和生活的痕迹。
只有真正的虎城老居民还留在这里。公共墓园就在县城中心公园的旁边。我猜想它原来也许是在县城边缘的。只是县城变得太大,祖先的鬼魂们只好待在热闹的中心地带,不得安宁。
他指给我看他们家的老房子。拆迁进行到一半,不知道原来是几层楼的房子,剩下两面一米多高的墙。家具残骸不得体地暴露,像他父亲坦然地露出棉裤。他小时候睡过的床,只剩下发黑的木头,也许就在里面。石灰、红砖和水泥块堵住半条胡同。他小时候生活的这条胡同,现在只剩下一半。另一半并没有消失,只是我看不见了。
没人住在这半条胡同里,至少我没有见到一个人。胡同旁边,是公园和墓园。三天后,我将随他们家人去祭拜家祖,那时我并不知道我的春节行程里还有这样一项安排。我认为那不是太妥贴。
一个真正魔幻的国度,空气闻起来有焚烧有机物的味道。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这是除夕夜的晚餐前最激动人心的时光,如同报幕后大幕仍未开启需要屏住呼吸等待的那一瞬间。
在半条胡同,我从他模糊、复杂又诡异的表情上,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一个男孩如何成为少年又如何变成眼前的男人?我以为自己对他很熟悉,其实一点儿也不。我对男孩、少年和男人们的生活,从来也不熟悉。所以我二十一岁才开始第一次恋爱,举步维艰地摸索着男性世界的点滴,时常感到挫败,不知道他喜怒哀乐的微妙变化为何会让我不得安宁。
我在大三暑假认识他,他已经是工作几年的老摄像。我不记得他那时的样子,只记得沉甸甸的思坦尼康机和响声很大的北京吉普车 这足以让任何一个年轻男孩看起来像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我无法抵挡。在我渐渐熟悉自己的新身份、明白恋爱这件事并不会都是甜蜜的时候,我才终于承认他不神圣,像我曾经以为的那样,是世界上唯一完美的人。他和我身边那些自私、傲慢又矛盾的自卑着的男孩一样,在北京的日常洪流里被迫翻滚。他时常在深夜被制片人电话叫起,然后去给一些什么人当代驾,或者天没亮就呆在中关村的立交桥上,等着拍早高峰的堵车,他在新发地批发市场拍禽流感专题的时候,被菜农砸了车,不久在拍天价物业费的时候,又被黑物业扣押了思坦尼康⋯⋯他没存下什么钱,每月工资到手要谨慎地装进各个信封,那上面分别写着房租、日用、存款、给父母、应急⋯⋯他像对待那些信封一样,分门别类地对待着生活、工作、爱情,或者还有眼前的家乡。我也许只在他的其中一个信封里,那些另外的信封,永远与我无关。在他被黑物业以非法拍摄的名义扣押了思坦尼康的时候,我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协助。 一台思坦尼康,就是一台捷达。 他说, 如果电视台要我赔钱,我需要免费干好几年的。
干燥让这里的天气预报失去权威。零度的空气没让我真正清醒。他们家的暖气太热,我穿着毛衣出的那些汗,现在还在羽绒服里。它们无法散发,像是没有出路的我、没有出路的我们,在天色转暗的墓园边,没什么目的地乱走。这也许只是我的想法。他应该想得更多。可是他没说过什么。他说, 带你去逛逛,家里不好玩。 我以为他说的是我,现在我想,他可能说的是他自己,他在 家里不好玩 。
坐上出租车回县城边缘他们的新家时,天空真正露出黑暗面目,大地上的零散灯光反而显出人间万象的气息。我问他, 你在老房子住了多久? 他想了想,心不在焉地说, 一直住在那里。 我还想问下去,但他看起来不想说话。
我暗自希望自己可以坦然接受韭菜饺子的味道、忽略脱掉裤子的他的家人们,像我在北京面对那些不堪忍受的事情时一样,相信那不过只是一时一刻,而我想要的东西,在那永恒的前方。
5
他的妈妈,热情邀请我也脱掉外面的裤子, 那不难受么? 她忧心忡忡地问。我完全相信她内心的真诚。可是我怎么能做到呢?在别人家只穿一条紧身的黑色打底裤,炫耀着并不好看的腿部线条?他的妈妈,后来把劝说我脱裤子的任务交给他,也许她是从这时起断定我不过一个娇宠固执的姑娘的。她对我的热情在那个冬天从未减退,因为她骄傲地向所有亲戚们宣布我来自南方,现在和她的儿子一样,在北京工作。南方和北京,像两个亮闪闪的奖章,一直别在我胸前。
他询问我的意见,他在很多事情上都在尊重着我。我想这并不容易,在那样的时刻。尽管他或许也希望我能入乡随俗,脱掉裤子。我猜想我也抱着同样的希望,这渺小的细节,会让我立刻融入一个陌生的家庭,至少看起来是的。
我抿着嘴以最小的幅度摇头。他说, 你理解一下,他们习惯这样,其实,你不需要脱掉牛仔裤的。 如果不是我全身都在出汗,也许我那时已经哭出来了。牛仔裤在身上越来越紧,我几乎可以感到,这让他母亲有多么奇怪,虽然她再也没有提过让我脱裤子的事情, 希望你在我们家待得舒服些⋯⋯ 她后来这么说,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指这件事。
茶几上大小不一的盘子都装满饺子,韭菜馅的。他们父子喝着虎城的本地酒。热气让窗户模糊了,我看不清那些炸裂中的烟火。我没有喝酒,但我相信我已经满面通红。汗水让我的头发更服贴。毛衣上已经可以闻见汗水、韭菜、烟、白酒的混合味道。我已经不介意了。这不是我还能顾及味道的时候。
酒让男人们话多,也更难理解。我相信他们在同时说着五个话题。他音调变高、语句流畅,像真正的节日里的人一样,喜气洋洋谈论着自己壮志未酬的事业。我从没听他用 事业 这个词说起过他的摄像工作。他最多用的词,是 活儿 , 今天有个活儿,明天没活儿 ,仿佛他从事的是某种复古的手艺,总是不耐烦地去做一件又一件重复的活计。
但现在他说, 还年轻,累几年,积累经验嘛。 然后他说起的事情,我只听过这仅有的一次。他说其实很忧虑电视业的前景,希望积攒一些资源,或者多拍一些作品 他也从没把那些电视新闻称作作品。合适的时候还是得创业的。当老板,开家影视公司。民间影视。听起来多么诱惑人,像个真正的梦想了。最初当然要天使投资,他很有信心。运气好,可以多轮融资,最终,必须要创业板上市⋯⋯当然,那不会容易,但马云马化腾乔布斯扎克伯格,他们成功前,谁说得准呢。
他脸面通红的父亲说, 踏踏实实,我年轻的时候⋯⋯ 。
烟火把我的父母在电话里的声音淹没了。我只能听出他们在说话,却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他们那边似乎没有其他声音。我想他们听见的情况,也许刚好相反,外面轰轰烈烈的爆炸声,听起来该是热闹的。我中气不足的声音无法穿透电话抵达他们的南方。我去了卫生间,看着镜子想,无论如何明天也要洗头。我终于听见他们的声音在手机里传来,远远地带着冰雪气息。
我们很好,在看春节联欢晚会,你在看吗?
我也在看。 我答。
他们或许开着免提,因为两个人经常同时说话,这是爸爸说, 还好今年没回家,你那么怕冷,不过,那边时不时也很冷?
妈妈接着说, 多穿衣服,不能只顾好看。 这是她永远都会说的话,从我上小学的第一天,到我大学毕业,只要我们有机会说话的时候。
我说, 他们家有暖气,不冷。 我不会告诉父母,他们家的暖气有多热,像南方的夏天一场预备已久的暴雨之前,那时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仿佛都集中到一起来了,沉重得让人相信呼吸是最困难的事情。现在,那时不时可以让房子轻微颤动的大火力鞭炮,是否是大雨将至前的雷鸣?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不对他们说出那些真正困扰我的事情了,我希望他们继续相信我害怕的不过是寒冷。
那真好,真好,有暖气。 他们又同时说话。
他们也许和每一个夜晚一样,两个人守着我们的小房子。那并不宽敞规则。拥挤的南方,人们为在山重水复间平整出一块适合居住的平地耗尽智慧。在县城,他们延续着这样的传统。在小巷两边层层叠叠的楼阁间,巧妙拼接着一个个家庭。那绝不相同,像七巧板千变万化、机关重重。他们永远让电视的声音保持在微小得不过刚好听见的音量上,因为电视墙背面就是邻家老人的卧房。他们总是需要应付各式各样的人,不时上门的邻居、窗外经过的人⋯⋯他们永远让自己穿戴整齐,像是马上要去参加面试。在南方最热的那些天,他们穿长裤、扎皮带,衬衫扣到上面第二颗纽扣,像某种宗教徒绝不放纵。我青春期的那些年里,爸爸习惯穿一件严肃的有白色滚边的咖啡色睡衣睡觉。我也是,我的白色睡衣永远是长袖长裤,和我的校服难以区分,好像我每天只要从床上爬起来就可以直接去上学一样。
我想,他们一丝不苟地穿着最厚重的那件冬衣,那也许并不是特别厚,两个人围着围巾,认真地吃简单的年夜饭。从电视细小的声音里,他们感受着除夕的气氛。两个人也许讨论再三,才提心吊胆打来电话。妈妈会把电暖器拎到电话旁。在南方冬天,做任何事都需要勇气,因为伸手的动作,便是彻骨寒冷的开端。他们会因为我在一个有暖气的地方感到宽慰,试图互相打消掉对方心中因为没有见到我,而产生的那种沮丧。
我忘了我还没有合上手机,一阵巨大的鞭炮声过去后,我听见他们不断地 喂,喂⋯⋯
妈妈,我听见了,我刚只是在想,也许我该洗头了。
妈妈说, 大年初一不要洗头!会把好东西都洗掉的,我们南方的规矩是大年三十洗头,洗掉不好的东西嘛。
我很困惑,这和他 除夕不洗头 的规矩完全相反。但我不打算告诉妈妈,因为我已经决定了,再坚持一天。不然还能怎么样呢?
6
我们后来的平静分手,时至今日我也说不清楚具体缘故。那几年的生活像加速播放的胶片,交杂错乱的情节扑面而来,却并不会真正留下印迹。虚幻的光影让我们面目全非并终于陌生。他始终没有投身那晚自己慷慨陈述的 民间影视 事业,事实是,那晚之后他其实再没提过这回事。我们在北京出租房的生活和过去的那一年相比,似乎也没什么变化,仿佛春节之行并没真正发生过。
有一次,他洗完澡站在镜子前擦头发,身上只穿着一条单薄的睡裤,露出已经开始发福的上身。这是寻常的景象,我猜想天下每个男人都是这么做的。他会一年一年一天一天地重复这动作,就像我重复刷洗仅有的一双黑色羊皮高跟鞋。我们都在向重复两个字妥协,像虎城化工厂传送带上的东西,永远不会与日常的洪流逆向而行。但那时,我只想起了他的父亲。他们身影相似,像是同一版胶片在不同年代冲洗出来的两个版本。他的父亲,穿深蓝色棉裤、一只手背在身后,弯下腰来,用另一只手努力擦干净新铺的地板上一块细小的污渍。
那年春节,他父亲说自己当过知青, 在你们南方的水田插秧 ,那时他 希望最好一辈子都不要再弯腰了 。他努力向我解释双脚站在水田里的那种寒冷, 好像那都不是自己的脚。 他说自己从那时才开始怕冷。他在工厂的那一阵,也许是最风光的时候。因为 他妈妈,当时在厂里打杂,那时候我们认识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都是这样的 。他没有再告诉我的那些后来发生的事情,我想只是因为他认定那不值一提。他们一起下岗,开始经营一家小超市,在必然的拆迁中搬到县城最边缘的房子。他们并不需要特别做什么,因为做什么也没用,重要的也许是一家人吃饺子喝酒的时候,他们还能说一些让彼此高兴的话。
他后来也离开了自己 不看好 的电视台,在无数个 临时 的工作后终于渐渐从我的世界里完全消失。我们分开的时候,他仍然相信 北京有的是机会,要做好准备。 只是我再也无法从这种话中获得力量。我也已离开了可以代订火车票的公司,在本来就简陋的简历上仓促留下一条不体面的痕迹。那时我以为这会是严重的事情,就像分手带给我的感觉一样。
我们间的缝隙,在那个春节的除夕夜便已开始出现。因为暖气带来的虚假炎热,让我们无法靠近彼此,于是我们只好在同一张床上尽可能地远离。我想,隔壁他父母的房间里,也许很多燥热的冬夜都上演着这样的场景,各自入睡,让彼此拥有清凉的梦境。我不知道他的父亲,是否还会梦见南方的水田,那刺骨、无法忍受的冰凉,尽管残忍如同现实的面目,却还是他最愿意对初次见面的年轻姑娘,提起的往事。
我现在住的房子,装有恒温恒湿的设备,这让我再也不会去考虑冷暖间的差别。那年冬天他们炎热的家,也不过成为一些很难被想起的陈年记忆,因为眼下的我需要面对的问题,其实并不比当初更少,或许还更复杂。那时,每当我走出他们家,进入一个真实的北方,从酷热到严寒的刹那转变,总让我有种穿越时空的错觉。
汕头治疗牛皮癣费用早期佝偻病症状四川治疗男科费用
汉森四磨汤口服液适用人群东莞白癜风医院排行榜
痛经量多是什么原因
- 下一页:DeeMind新论文缘由
- 上一页:Axle发行1
- 06月21日奇幻给狗狗清洗耳朵不配合怎么办图位置
- 06月21日奇幻给狗狗怎么驱虫位置
- 06月21日奇幻给猫咪洗澡的七个注意与十个步骤位置
- 06月21日奇幻夏季饲养杜宾犬如何防过敏防中暑位置
- 06月21日奇幻给猫咪按摩有什么好处位置
- 06月21日奇幻给猫咪吃自制猫粮好还是自制猫饭好位置
- 06月20日奇幻狼青幼犬流鼻涕是怎么回事位置
- 06月20日奇幻猎狐犬呕吐怎么办猎狐犬感冒发烧的治疗方法位置
- 06月20日奇幻猫为什么乱叫家长以包容的态度去面对位置
- 06月20日奇幻猫不喜欢什么味道位置
- 06月20日奇幻猫咪上呼吸道感染的病因及诊断位置
- 06月20日奇幻狼青犬的缺点是什么狼青犬的缺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