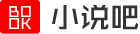聚散两依依总有一种旋律让我们难忘离别四十
自建群后就发起了“故园寻梦”聚会的邀请。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和等待,终于迎来了四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在黔西岔白农场“情真聚首,时光倒流”的欢聚。
在杜鹃花大酒店初次见面的那一刻,别提大家那个高兴劲,握手,拥抱,激动之情无以言表。
目睹此景,瞬间打开了我的记忆闸门,想起了那些年父亲在岔白农场负责劳改工作的艰苦岁月,更想起了儿时在岔白农场的诸多生活情景及种种趣事…
放眼四望,此地是一片特殊分野的领地,又是一方守望赤诚的所在。伫立此间,遥忆难忘岁月,悲壮的往昔破浪而来。五十年前,岔白偏僻荒凉、人迹罕至。
应该说,“劳改农场”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新创造。当时社会情况比较复杂,政府掌握的物资又比较匮乏,无法一下子把所有需要改造的罪犯都押解到。于是司法机构将需要改造两三年左右的人送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教育,让他们在改造中清除剥削寄生思想,养成劳动习惯,学会生产技能,变成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基于这一历史背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一群以“西进”和“南下”为主的操着不同口音却有着共同目标和意志的转业军人,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当时较为偏僻荒凉的岔白农场,同罪犯一道,搭帐篷、睡地铺、啃窝头、烤红薯、烤土豆。他们身背、手提、肩扛,执着挺进,吃苦耐劳,尽责担当,继往开来,在一望无际的岔白旷野上,从艰苦与险恶的绝地中,拓荒垦植出一片近三万亩田土的“农场”建成了毕节地区最大的农场,成为贵州改造罪犯的重要基地之一。在为巩固国家新生政权和社会稳定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同时,也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芳华献给了那片土地。
曾经的岔白农场是庄严的,也是激情的。老一辈人爱唱一首歌:“我们的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呀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这是老岔白人的心声,更是老岔白人自身的写照。为什么提到老一辈人励志鼓劲的红色传统,我们眼里总是噙满泪花,因为老一辈人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岔白人远离繁华,直面闭塞,甘于贫困,忠于职守,正因为有了老岔白人创业艰苦卓绝的过往,才有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巨大成就。在这里,多少服刑人员自学成才,成了发明家,多少服刑人员变成农艺师,多少服刑人员成为书法家、画家,多少服刑人员文笔滔滔,著书立说,在这里,也有刑满留场就业人员的子女,有的当了职工,有的当了民警,所有这些都值得可喜可贺,也当值得欣慰,因为这是社会进步的写照,也是一种法制平等,更是一种国家胸怀…
感悟岔白时间长河的流转,有陶冶心怀的澎湃与洗礼,感悟岔白人,总有一种旋律让我们难忘,总有一种激情让我们感动,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奋进,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昂扬。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历史如烟云般逝去,我们的父辈大都已离开人世,而作为这群军人后代的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对这片故土的依恋一点不亚于我们的父辈。
当年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懵懂少男少女,在一起度过了最纯洁、最真诚、最天真无邪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操场上、教室里,山间田野,山林里,海子边,嬉戏逗乐,疯打疯闹,时不时还出现恶搞,或翻墙偷吃邻居家葡萄;或模仿渡江侦察记中解放军夜袭敌军的动作,趁看管果园犯人不注意,潜入农场果园和庄稼地偷摘西红柿、香蕉梨、苹果梨。
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无忧无虑享受年华,那时我们都很单纯,但也无奈,物质匮缺,生活艰辛,吃顿猪肉很是奢侈。记得有回陆伯伦和郝建伟去给家妈看家,那时在县氮肥厂上班,家里没人他俩趁家里没人,几天时间就把人家一大坛猪油吃个一干二净,他们倒是肥腻了肠胃,可是在那个以供给制为主的计划经济年代,却害得人家李老伯妈苦熬了几个月的素食,现在回想那时的恶作剧,不无后悔;同样,那时想谈恋爱也是很奢侈的,黑白的青春,男女同学有相互交往的并不多,很少说话,如果能听到一个女生或一个男生相互说话,那绝对是“有故事”了。十多岁的男女或许还有朦朦胧胧、羞羞答答的感觉,没有人去表白,没有人去追求,但也不排除个别少男少女恣意挥霍,风流作别,在心中埋藏着一个小秘密,如若不信,二大队那间被称为“恋爱房”的小木屋就是最好的明证。
不谙世事的我们最终长大了,长大了的我们刚踏入社会就遭遇了时代的困惑。六十年代,单一的经济体制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为了缓解城市的压力,在结合国情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就业门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此,知青作为一项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的长期工作被确定下来。这一“机遇”正好被我们这一代人赶上,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命运注定,我们满怀理想和激情,追随历史潮流,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向着岔白聚拢,开始了人生的新起点。
我们一干就是两年、三年,甚至还更长,饱尝了离乡背井、远离亲人的苦涩、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生活艰辛。正当我们在前途问题上处于彷徨迷茫时,国家很快对知青落实了政策,陆续出现的知青大返城瞬间又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同时也打散了我们这个集体。大家各奔东西,纷纷踏上了追梦之路。有的穿上了军装,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有的成为百年树人、桃李满天下的人民教师;有的在异地他乡继续干老本行当警察;有的则成为保驾护航的人民检察官;有的继续留在农场,依然在那片土地上耕耘劳作。再后来,随着岔白农场的撤销,人员四散,疏于联系,加之各自为家庭事业忙碌奔波,见面的机会非常少,即使个别偶尔相遇,也都是见也匆匆,别也匆匆,以至于一别40年终未能见上一面。
岁月如歌,时光流逝,转眼间我们已近花甲之年。在体味了人生五味,历经了世事变迁之后才发现,灵魂深处最依恋的仍是那片故土,最难忘的依旧是那份发小情、同学缘、战友情,如一坛老酒,历久弥香,回味无穷。
聚会把每个人都拉回到了从前,回到了十分值得我们怀念的童年、少年时代,每个人好像都还只有十多岁,真挚的情感、纯真的友情完全迸放出来,没有虚情假意,只有浮想联翩,没有任何功利,只有纯洁之情。
我是谁?是你在问?/还是我在问?
哦,我们都在问。
美女,帅哥,/已然需要冠上“曾经“/岁月的侵蚀,/让鬓角平添了几许银丝。
生活的磨难,令眼角爬满了皱纹。/想不起,记不清。/没关系,我们之间有一条纽带,/以前都是岔白人。
剪不断,理还乱,/不是亲情,恰似亲情,缘入骨髓忆也深。
发小,和泥的玩伴。/发小,无谓羞耻的童真。/发小,前生注定的情缘。/发小,原生态的清纯。
噢,那深沉的红色,是玫瑰还是拉菲?/哦,那是被火烧过的云。/那是很想留住,却总是从指缝间溜走的光阴
海鹰,当年岔白农场的“场花”早年只身闯荡海南,酸甜苦辣尽尝,一别四十年,重逢之时,郝国庆作词为其接风:当年寻梦赌芳华/只身渡琼峡/四顾烟波接天/何处是归家/文昌鸡/加积鸭,且由它/身在椰城/心系黔中/魂牵那大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分别时风华正茂的一群少男少女,而今已是两鬓斑白、华发苍苍。
多年未见,纯真的友情如同久违的亲情。
这人好面熟—天哪!这不是“阿四”吗?
无形的眷恋将大家从天南海北牵回了这魂牵梦萦的故地。
站在大海子、老基建队、修理厂一带,回想当年成长和战斗的足迹,感慨万千。
寻找场部办公楼、礼堂、学校、老住宅旧貌。
忆往昔,往事如风恍若昨。
办公大楼左前方有一片松林,那是儿时玩闹的地方。
这不是当年的家属居住区吗?想当年拿着一个碗,吃东家喝西家,最后连碗放在谁家都记不清了。
还记得球场上看露天吗?每当听到高音喇叭中传出郝老伯的声音:“今天晚上放,各家各户自带小板櫈”小伙伴们那个乐啊,早早的吃完晚饭,拿上小板凳占个有利的位置。那时《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不知看了多少遍。
儿时常去玩耍的“老地方”—荷花塘,这是记忆中最深刻的地方,因塘中有一片荷花而得名。
这里曾是洗衣挑水的地方,也是儿时游泳和垂钓的好去处,每当夏天来临,塘中开着洁白的荷花,伴随着蛙鸣声,一群小伙伴在塘边垂钓正欢。有一次,小女孩小喜元来观看,大呼小叫:“吃了吃了,快点快点。”小鱼儿嫌其吵闹,叫她走开,小喜元嘴一嘟哝:“公家的塘子,又不是你家的!”小鱼儿无奈,只好拿着鱼竿乱甩一通,只听“唉呀”一声惊叫,鱼钩正好钩住小喜元的左眼皮,吓得小鱼儿扛着鱼竿赶紧牵着小喜元到医院去取出鱼钩,从此小喜元的眼皮留下了一道小小的疤痕。
不知从何时起,塘子开始颓唐起来,渐渐的连荷花也不见了,再后来,塘子变成了臭水塘。
这是当年的二大队。这幢白色的土墙楼房可是岔白农场建场的标示性建筑,始建于一九五三年十月,见证了岔白农场的兴衰。站在楼前,仿佛还看得见当年那满天飞翔的鸽子。土墙楼的旁边还有那幢令人起敬的小木楼,几家老岔白人在不同时期都住过,而今成了保护性建筑。
这是当年的医务室
很多地方早已是面目全非了,已没有了当年的影子,惟余淡淡的一丝儿时记忆。
曾经,这里的几十栋房子凝聚了父辈们血汗泪,除了部分房子当地人住着,好些房子还空着。
最能显示男孩子胆量和气魄的要数老学校后面的大海子,那可是几个大男孩搏浪和展示雄性气慨的绝佳场所。站在高高的石坎上,大有“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英雄气慨,记得有一次小阿榴、小志安在水中赤条条的玩得正起劲,不经意间回头看见背后岸上站着威严的王老师和几个男女同学,顿时吓得慌忙上岸穿衣,可衣服却不知去向,赶紧又回到水里藏羞…。
正宗的发小在这里,四十三年的复制,能还原当年的情景,却还原不了岁月。
上图:左郝国庆;右王爱平
下图从左至右:吴拾庆、王成智、吴俊洪、郝建威
我们高中岔白三同学,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文章开头黑白照片上那位身着上白下蓝制服、腰上撇杆手枪、英姿飒爽的美女—翟广云,还有一位叫程华的不知去向,至今联系不上。
认出中间这个“高大上”吗?对,张志学,是他。当年好酷的英俊少年,一双黑白分明一尘不染的白边鞋,曾是不少怀春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
意犹未尽的笑容还在脸上,短暂相聚的激动还在心中荡漾。
回忆小时候的点点滴滴,尽情倾诉各自的人生经历。
相识是一份缘,相逢是一首歌
冯青云:“来喽,我们俩发小,从小一道学抽烟,一个烟撇成两半,这种感情不喝要得个鬼!”
举杯痛饮,愿友谊地久天长。
这杯酒在漫漫岁月里制酿,在四十年时空中窖藏。
相拥不一定“有故事”不信你们可以确认眼神。
用手架起彩虹,为你遮风挡雨。
酒兴正酣,情到深处。
已经找不回岁月,那就好好珍惜当下吧!
点燃了心中的火把,我们尽情地唱吧!
丰盛的宴席,亲切的交谈
当年的发小、同学、战友全都,至今留下顾小苏一人“看守”农场(下图右三)
四野部队十五兵团四十三军、十二兵团四十军子女合影。
当年的知青合影
当年医务室的五朵金花
此次聚会,出现了不少动人的场面,冯东霞第一天刚下飞机和大家见上一面,突然接到单位电话,又不得不迅速返回海南,带着牵挂和思念之情风风火火地把手头上的工作处理完后,又马不停蹄地往黔西赶…
石贵萍为了能和大家相聚,百忙之中从贵阳赶来,最后一晚和大家相见,激动、喜悦之情无以言表。
好些最初因有事来不了的,在群中看到聚会的氛围,仿佛回到了从前的时光,激动之余不愿留下遗憾,想方设法赶到,使得聚会队伍不断壮大。
彼此想说的话太多,聊不完的前尘往事,说不尽的离情别绪,道不完的喜悦与沧桑。
为了这次活动,冯海鹰为大家制作奉献了35件精美的T恤;周大勇、万碧珍、刘柄辉诚邀大家共享K歌和酒宴,也有好些群友热情主动提供酒水,可谓情深意浓。
谢谢这次聚会的发起人、组织者郝建威、冯东霞,为大家搭建了相聚的平台,没有这个平台,就没有这三天聚会的精彩、欢乐和开心。
才见面,又要散,恨时光太短暂,相聚太匆匆。
岁月总有一个场景,出现在依依离别之时,惟愿时光芬芳,落花静好。
口服液算是适合儿童的剂型吗
脑梗死恢复期的饮食以及药物有哪些
- 下一页:愿做秋天里的一片落叶
- 上一页:咏毛泽东主席十二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