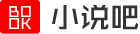国家坐骑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马这一动物形象的文化崇拜由来已久,周穆王驾八骏之驹 日行三万里 , 东游沧海、西驰昆仑 ,平定四海;秦始皇统一天下是用七骏;汉武帝 虽远必诛 征战西域用的是十骥;唐太宗李世民则一生挚爱坐骑,留下了昭陵六骏 丰富的马文化不仅让世人看到具象的马的品性,也寄托了抽象的道德情感,正如《论语》中所说: 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如果说在历史长河中马承担了国力的象征,那么到了巨变动荡的近代它又会扮演什么角色?甘肃作家李学辉是武威人,正是出产良驹的古凉州所在地,在近期推出的长篇新作《国家坐骑》里,他钩沉出了近代历史中发生于凉州城的一段烛照家国精神的故事。
这个故事已在李学辉心中盘桓了十年,凉州自古产好马,他素来知晓,但随着接触越来越多武威当地流传的凉州口述史时,他开始意识到其中隐藏了许多有价值的素材,他注意到在1927年凉州大地震之前,遍布凉州城乡的马神庙就有20多处,从事养马职业的人更是众多,而这些与近代史的转折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关联。由此,一个关于 义马 的人物形象逐渐成型。什么是 义马 ?小说的前半部分把重心放在 义马 的诞生和养育上,在李学辉笔下,凉州城马户中,有一批专吃 义马粮 的,他们一出生便接受严格的检测,若体格坚实、耐力强大,便被作为 国家之马 的储备供养起来,死后焚化作为马形,意为来世转为 国家之马 ,为国效力。
在当代文学的人物谱系上,这是一个全新的文学形象。小说中一出生就顺利被相马师检测认定是 龙驹 并改名为韩义马的角色,有着传奇的色彩:为了符合 义马 的标准并成功成为 国家之马 ,韩义马经受了一系列的训练,他以半人半马的方式生活,并在精神上也完成了人马合一。李学辉对记者表示,在构建 义马 过程中,他首先要避免的就是猎奇,他将历史时期定在了189 年到1927年之间,中间发生了清朝覆灭、军阀割据、凉州大地震等重要历史事件,韩义马以及他身边的人一同在历史动荡里沉浮,他却始终被守护着,直到最终的祭典仪式。
诞龙驹,养义马,是小说中所有马户及马政司最关心的问题,他们延续着传统文化中对马的崇拜,相信 国有兵才稳,兵有马才胜,家无马不兴 。特别是当时的国家已被普通民众认识到积贫羸弱,挡不住外来的坚船利炮,寄希望于 龙驹一出,天下大兴 。显然,依靠固有的养马方式并不能诞生被寄予厚望的 国家之马 ,只有注入人的因素才有希望完成, 义马 在李学辉看来更是一种民族精神的承载, 人的智慧和马的忠诚合二为一,形成一种精神支撑 ,这种支撑对于当时的大众而言是一种非常迫切的需要,培育 国家之马 的过程也成了民族精神 还魂 的过程。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郭艳在看完这部小说后便评价,这个形象构建是 让一个负载着盛世文化符码的人马在乱世中复活,让艰难生存中行尸走肉苟活的人们看到中国人文精神的一缕魂魄 。
在近代大众身上寻找文化精神并非易事,近代知识分子往往认为 国民性 是一个需要被改造的对象,从传统国民到现代国民,要经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转型过程,其中经受外界的启蒙更是起到重要的作用。在小说中的马户群体身上,读者明显感受到他们身处传统文化的惯性之中,一切以朝廷的命令和意志为准,身负的使命也流露出宿命感,而这种顽强的使命意志可以抵抗住时代剧烈的变化而矢志不移。在李学辉的观察里,身处时代转型时期的传统民众身上有着盲从、逃避、毁坏等心理,此时 国家之马 对于大众的意义也是复杂的。 只有一个强大的梦想才能使他们的精神重启,这更需要有强大的力量来引领。尽管如此,但大众还是存有一种向往。 国家之马 ,就是要让民族精神的另一面升腾,使传统文化惯性中的闪光点复活,进行重新配置。配置是一种痛苦或艰难抉择的过程。这个过程对大众来说,还要打破从众心理。
小说中几段对国家观念的讨论呈现出作者对于这种复杂性的思考。因为韩义马身上承载的精神召唤力量,不同权力者都希望他为自己所用,到了马军长以当地军阀之姿控制凉州城时候,便和守护韩义马的圉人进行了争辩,圉人说: 在整个冷兵器时代,我们民族的属相是马。这种刚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要留给国家。 类似的讨论在小说中还有多处,反映出典型的国民意志和国家意志,在圉人以及韩义马周围的人身上,有一种执着的国家意志,他们将传统文化中的忠诚、仁义倾注在 义马 身上,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培育了作为 国家之马 的 龙驹 ,并且时时体现出牺牲精神和契约精神。在李学辉看来,相对于鲁迅笔下人物的国民性, 《国家坐骑》中人物的国民性,有一种超越普通民众认知的特性,牺牲和契约精神所引发的悲壮,会起到发人深省的作用 。而这,或许是传统文化埋藏在普通民众身上内在的启蒙力量,这也触发了他进一步希望读者思考在小说后半部分提出的问题:圉人国家观念形成的原因和根源是什么?如何看待圉人国家观念的出发点和动机?如何重塑一种刚健的国家精神?
这些关联起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思考不仅体现在《国家坐骑》里,也在李学辉之前的多部作品中有所体现。在 麦子三部曲 《麦婚》《麦女》《麦饭》中,读者看到了奇异的风俗背后是民众对粮食的文化崇拜。在《末代紧皮手》中,借由土地祭祀这一古老职业讲述了土地与人的精神关系,它们存在的问题既是过去的也是当下的。《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认为,李学辉的这些作品 重心不是写历史、政治和文化,也不是写志怪游侠传奇,是人和风俗的合体,带着特定的民间风俗文化和现代历史经历 ,并且 一定感知到了土地上那已经失传的民俗生活但是并没有断根的文化心志 。李学辉对记者说: 近年来,我写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打捞、挖掘业已消失的关乎百姓生存或信仰流失的传统文化。我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之复活,而是为了探究根由。这些看似民间信仰的东西,在大文化的格局中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割裂或者摈弃,对承继传统文化的优秀及贯通古今文化气息都会带来认知上的偏差和误区。
古人说西北 黄沙风卷半空抛 ,而 马渡冰河渴自跑 ,似乎也可以用来比喻文化根脉在不同历史时期自由漫延却缺乏有效的导引。当文学一次次触及到文化中根本的灵魂之地,与之对话,观其困境,活化气息,也就有可能提取到它最本质的精神力量,创造性转化出当今社会需要的文化心志。
|长春治疗白癜风方法什么食物消肿止痛化淤患上术后ED该怎么办- 06月21日现实给狗狗戴脖圈和牵引带好吗位置
- 06月21日现实给猫咪洗澡的步骤及建议位置
- 06月21日现实夏季饲养松狮犬注意事项位置
- 06月21日现实夏季饲养哈士奇注意事项帮萌萌哒二哈过凉爽位置
- 06月21日现实给猫咪喂食三文鱼好吗猫咪是否可以吃三文鱼位置
- 06月20日现实狼青幼犬的良好性情培养位置
- 06月20日现实猎狐犬幼犬社交活动不可少位置
- 06月20日现实猎狐梗好养吗一般家庭怎么喂养猎狐梗位置
- 06月20日现实猫不是通过味道来判断食物的位置
- 06月20日现实猫咪上火了应该怎么处理位置
- 06月20日现实狼青犬皮炎和湿疹的诊断和治疗位置
- 06月19日现实狗狗断尾的原因与注意事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