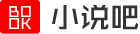冯家海子
疆字906部队往事回顾 4
冯家海子,我心中的一首歌
冯家海子,我心中的一首歌。
冯家海子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准噶尔盆地的南缘,兵团农六师所在地五家渠市的北部。她,碧水蓝天,波光粼粼,芦苇一片连着一片;她,野鸭成群,鱼翔浅底,湖边覆盖着一层又一层雪白的盐碱;她,倒映着天山博格达峰的身姿,美轮美奂,简直就是童话世界的再现,塞上江南的一个缩影…
不过,今天的人们,再也见不到她的身影了。这座美丽的湖泊,已经淹没在快速发展的城市海洋里。
然而,她依然是我心中的圣湖。就像过去的几十年一样,她牢牢地镶嵌在我的脑海,清晰地萦绕在我的梦中,永远歌唱着美丽的旋律。
上世纪70年代初,作为新疆军区疆字906部队的一名战士,我在她的身边度过了3年多的光景。艰苦的训练,火热的生活;战友的情谊,首长的关心…给我留下了许多永世难忘的印象,可是,最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是这座伴随我度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戈壁湖泊。
首次与冯家海子相识,是1971年1月11日清晨。那天,是我进疆后迎来的第一个早晨,我和一同入伍的许多新战士一起,排着整齐的队伍,踏着叽叽作响的白雪,从临时居住的农六师八一俱乐部出发,到即将分赴的连队去就早餐。从农六师师部到连队大约有1.5公里的路程,到处是白花花的世界,连我们的眉毛和茸茸的胡须,都被呼出的哈气染上了白霜。我们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一边高喊着口号,一边向北走着。当离开城区不远的时候,突然,我发现左前方有几个与我差不多年龄的少年,正在白茫茫的广场上嬉戏,广场的周边,长满了成片成片干枯的芦苇。再仔细一看,那哪儿是什么广场,分明是一片结了冰的湖面,少年们正在尽情地滑冰。原来,我们正在经过一座小小的涵桥,桥的左边是一片开阔的湖面,岸上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林木;右边则呈河流状态,宽窄不同地蜿蜒着向东北方向流去。所有这些,都被厚厚的冰面和白白的积雪覆盖着,在枯黄的芦苇和洁净的碧空映衬下,俨然一幅北国风光,静谧而又神奇。吃饭的时候,我忍不住向带兵的龚明华排长打听那条河的名字,他用一口浓重的湖北话漫不经心地告诉我,那是冯家海子”从此,冯家海子”这四个字,永远占据在了我的心田。
我们的部队,就在离冯家海子几百米的岸上,北面,是茫茫的戈壁沙滩,荒凉而又浩瀚;南面和东面,则被这座称为海子的湖水所包围,风光旖旎而又景人。那些年,我们在海子边上训练,开垦荒地,谈心聊天,甚至闲暇之余在这里捉鱼观鸟,很是惬意。
夏天来临的时候,湖里的芦苇长得足有两人来高,一片连着一片,浓绿浓绿的,潇潇洒洒,密不透风,割了一茬又一茬;湖面,游弋着各种野禽水鸟,响彻着婉转动听的鸣叫,这群飞起那群落下,水花涟涟,风声扑扑。尤其是遇到晴朗的天气,白雪皑皑的博格达峰倒映在碧绿的冯家海子水面上,有密如帷帐的芦苇相衬,有清澈如洗的蓝天白云作陪,鸟儿在飞,羊群在走,那又会是怎样一幅美景?
半年之后,我从特务连调到了团部机关。由于行动自由,我常一个人坐在高高的白杨树下,沐浴着阵阵清爽的微风,一坐就是许久,尽享着塞上风光带来的愉悦。
冯家海子不仅风光秀丽,还给我留下了许许多多有趣的故事和回忆。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往事仍像刚刚发生过一样。
@如今,在原来桥西湖面那个地方,新修了一座公园,名子叫北海公园。园子里依然有不少芦苇,那一定是那个时候繁衍下来的(以下为秋海摄影)
故事一:爱狩猎的柏副团长。
柏团长个头不高,瞪着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走路有点八字步,满口地道的山东口音。他与许多团部首长一样,来自上海警备区,是我们这个部队组建时过来的。印象中他特别家常,吃饭的时候,最爱蹲靠在伙房前那棵树桩上,一边端碗吃饭,一边与机关的战士们聊天。他有一项特别的爱好,闲暇之余,常掂上那杆双筒猎枪,到冯家海子边上打野鸭。他枪法很准,常常是枪响鸟落。此时,随同看热闹的战士就会争着下水帮着捡拾中枪的禽鸟。我的战友、军旅作家郝洪山曾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这样描述柏副团长:一个休息日,我终于有了到冯家海子放飞心情的机会,当我满心喜悦地来到海子边时,看到有一位老同志正在水边用猎枪打野鸭子。仔细一看,此人原来是我们副团长。这让当时很少能见到团首长的我不免有些惊喜。据说,我们这个副团长是山东好汉,虽文化水平不高,但打仗尤其英勇。传说他有三大特点:‘打仗爱拼命,说话爱骂人,平常爱打猎’今日有幸亲眼看到我们副团长在此小试打猎的身手,不能不说也是我的一个意外收获。我正在想时,忽听副团长朝我喊道:‘哎!小子,你在那发什么愣?还不下水给我捡野鸭子。’副团长一声吼叫后,我忙不迭地便跳进了水里。
故事二:捉了两只小水鸡。
那是1972年的初夏,我担负着团广播员的职责,主要任务是通过高音喇叭统一向部队播放作息号声和征集编播各类宣传稿件。工作的特点,使我每天上午和下午,常有大块儿的时间供个人支配。有一天下午,刚从农六师学习放回来的战友康大选兴致所来,提议我们一块儿到南边的海子边儿玩一会儿。大选与我同年入伍,不但年龄相当,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年兵,还是坐着一节车皮来到部队的铁老乡。有人作伴去玩儿,哪有不去的事儿?我们连奔带跑,不足一根烟的工夫,就经过一个小桥,绕到了冯家海子的东岸。我们一会儿蹲在湖边的草丛看硕大的水獭从洞口进进出出,一会儿用苇杆驱赶隐藏在水草里成群的鲫鱼。突然,一阵叽叽的小鸡叫声吸引了我们。原来,在一片开阔的湖面中央,有一坨小岛样的草滩,两只野水鸡爸爸妈妈正带领几只金黄的小鸡,游弋在草滩的旁边,一会儿往北,一会儿往南。
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那上边一定有不少鸟窝!走,看看能不能掏几个野鸭蛋回来。我们迅即脱去军装,穿着绿色的大裤衩子下水奔草滩扑去。
这一带的湖水并不太深,有的地方没肚,有的地方齐肩,我们绕过水里一丛丛苇茬,转眼就来到草滩附近。
两位不速之客的造访,大大地惊扰了岛上的居民,它们瞬间尖叫着四散开来,有的扑棱棱腾空而起,有的携儿带女下水而逃。我和大选早已忘记掏鸟蛋的初衷,尾随着逃散的一群小水鸡就追。顾不得水草缠身,忘记了苇茬扎脚,连扑带截,还真的抓到了两只黄得耀眼的小鸡。它们毛茸茸的,浑身颤抖着,发出加加的叫声。随即,我们兴奋地跑回部队,来不及看看脚上和裤裆里被苇茬划伤的口子,忍着盐碱水的蛰痛,用脸盆打来清水,把两只可爱的小宝贝放在了里面。我们憧憬着,每天要捉些小鱼小虫喂它们,等把它们养大了再放回冯家海子里。然而可悲的是,也就两天的工夫,两只可爱的小家伙就在凄凄的叫声中先后一命呜呼,留给了我们许久的遗憾和歉疚,以至从此再不提捉鸟的事了。
@这就是我当年的战友康大选
故事三:上了杜玉林的当。
没有实地体会的人,可能根本无法想象,当年我们对冯家海子里曾经发出的怪叫,有多么普遍的疑惑。几十年过去了,每当谈起这件事儿,大家依然那么兴致盎然,惊叹不已。那叫声,就像风吹瓶口的声音,嗡,嗡…一下一下地不时响起,低沉而悠远。特别是到了夜晚,几里开外的地方都能清楚地听到。不少当地人曾经试图探究它的根底,可是,人们连声音发出的真正方位都搞不清楚。往往是你听到声音在芦苇荡的那边,但跑到那边时,声音又奇妙地跑到了另一个方向,最终全都不得其果。所以大家只好作出各种各样的猜测,有的说是一种大鸟的叫声,有的说是水老鼠的呼唤,猜测最多的则认为,海子里有一只巨大的蟒蛇,它深藏在茂密的芦苇荡里,靠逮食飞鸟和鱼生活,一定是它安静时发出的声音。
听了杜玉林的话,我心里虽然怵怵的,却也经不住好奇心的诱惑,即使冒险,也想亲历一下这刺激的发现。心里想,搞不好我们俩会揭开这个906之谜呢!于是,我顾不得多想,连军装都没脱,甩掉鞋子就跳到了玉林的筏子上。说时迟那时快,杜玉林哈哈大笑一声,他把撑杆使劲一推,我们俩便晃悠悠地朝芦苇深处荡去。看着茂密的芦苇从身边慢慢划过,想着一会儿可能遇到的惊险,我的心提到了喉咙口。也就在这会儿,身后的杜玉林又发出一阵哈哈的笑声,我还没来得及扭脸看他笑什么,筏子便猛地晃了一下,只见他又猛地一蹲,再把撑杆使劲往下一按,我一个趔趄就栽进了咸涩的湖水里。原来,我上了杜玉林的当,被他实实在在地耍了一回。等我一边抹去脸上的湖水,一边气喘吁吁地爬山岸时,得意的杜玉林早已跑到十几米开外的土岗上笑得前仰后合,险些从上边滑了下来。
有趣儿的故事还有许多,比如在冯家海子的冰面上学滑冰,在冯家海子边上的沙地里灭老鼠,在冯家海子的芦苇边垂钓,在冯家海子的河沟里看三连炊事班拦鱼,在冯家海子里游泳…可谓故事一串串,回忆一筐筐。这些就像一个个晶莹的明珠,点缀在我的青春岁月里,闪着永远的光。
@当年战友们在冯家海子边合影。左一为杜玉林
啊!美丽的冯家海子,你是我心中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
★ ★ ★ ★ ★
2017年1月28日(正月初一)
初稿于郑州
本文相关词条概念解析:
海子
海子(1964.3.24-1989.3.26),原名查海生,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当代青年诗人。海子在农村长大。1979年15岁时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2年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海子1983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工作,1984年创作成名作《亚洲铜》和《阿尔的太阳》,第一次使用“海子”作为笔名。7年的时间里,海子创造了近200万字的诗歌、诗剧、小说、论文和札记。比较著名的有《亚洲铜》、《麦地》、《以梦为马》、《黑夜的献诗——献给黑夜的女儿》等。另外也出版了《土地》、《海子、骆一禾作品集》、《海子的诗》和《海子诗全编》等等。
- 下一页:混沌剑神第六百二十四章对决圣王一
- 上一页:血魔真神 第12章 谈之色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