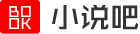边城之抒情印象(1)
在文坛上,大家都知道沈从文有两种相对立的题材:一种是都市社会题材,用来批判文明重压下都市道德的沦丧;一种是描绘湘西世界的题材,用来展示乡村理想的生命形式和生活状态。而其中篇小说《边城》就是描绘湘西世界题材的主要代表作之一。《边城》里,沈从文满怀创作激情,运用其独特的抒情笔调和叙述视野,构造了一组组充满诗性内涵和悲剧意味的画面,把读者们带入一个美丽无比韵味无穷的湘西世界。
一《边城》的诗性内涵。
从抒情内容来看,整部《边城》都洋溢着人与自然相互交融的诗性内涵。作品开头,作家以其灵秀俊逸的笔墨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优美多彩的人间画卷。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的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寥寥数语,简洁且诗意的文笔搭建出一副远离都市尘嚣的山水人家画面。而接下来的古城茶峒在笔下是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在这美丽宁静的大自然中,顺应着古城的葱茏山景和灵动水色,跃雀出了一位美丽羞涩少女,即翠翠。正如作品中描绘的那样: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到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翠翠这样完美人物形象的诞生当然离不开生机盎然的边城风景的养育;而生机盎然的边城风景因为有了翠翠这样美丽灵动的生命进而变得更加生机盎然。人即景,景即人,人景一体自然而然就构成了一幅百品不厌诗意蔓延的山水画卷。文本中传递出自然与人和谐共处,人与自然相得溢彰的诗性内涵。自然因为人的维护才保存了完美的现状,而因为自然的熏养才美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文中,不仅人物的外在形象和本真自然形态完美融合,人物的内在人格更是和本真的自然形态有机结合在一起。俗话说: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茶峒那醇厚的山和灵动的水,同样培育了一群淳朴善良的人们。这里的人们行善做事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都是发自内心的良善行为,而不需要外在的宣传和号召。
翠翠的爷爷即老船夫就是沈从文在小说中着力刻画良善人物的代表。在笔下,爷爷是一个勤劳善良、淳朴憨厚、尽职尽忠摆渡者。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大,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他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从不贪心。我有口量,三斗米,七百钱,够了”他乐善好施,夏天在准备一个大缸,把茶叶用开水泡好,给过路的人随意解渴!”准备了发痧、肚痛、治孢、殇子的草根木皮”给身体不适的过渡者用。他过节喝的葫芦酒,遇到相熟的马车夫想喝,也从不吝啬,必很快把葫芦递过去”他做这些事情并非是要得到别人的回报,而不过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良善和诚意,为此深得人们的敬重。在这个小小的边城,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淳朴良善的磁场,人与人之间总是能够以诚相待。水手、商人送红枣、送粽子给老船工,作为对这个忠于职守的划船人一点敬意”
掌水码头船总顺顺同样是边城里良善代表人物。他大方洒脱喜欢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对于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退伍兵士、游学文人墨客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在他的身上,少了都市人的自私和狭隘,少了商人聚敛钱财的贪婪和世故,少了奸诈小人的阴险和刻薄。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山里人豪爽耿直的胸怀,看到的是一颗仗义疏财的仁义之心,看到的是乡民的光明磊落品行。正是这种良善品德影响着这一方水土,从而在这块不显山不露水的边城小地保留了一份大都市人奢想不到的淳朴民风,并且这种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的淳朴民情在这古老的大地上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后人,演绎着一个又一个传奇故事。
天保傩送这一对兄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时心仪上了美丽纯真不明世事的少女翠翠。面对这样难以预料的尴尬,兄弟俩并没有争个你死我活,而是在山头一展歌喉来俘获少女心。天保为了成全弟弟傩送的爱情,主动放弃了对翠翠的爱,远走茨滩,不幸溺水身亡。而弟弟因为的意外身亡愧疚不已,有意压抑自己的情感,疏远翠翠。在这里,把爱情和亲情,生与死相互交织在一起,任凭读者慢慢品味这人性的善良和本真,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了的创作意图。
同时,在这片未被现代文明污染充满原生态风味厚土上,滋养了一群自觉自为担负的人。首先要说的就是船总顺顺。顺顺因为大佬天保的意外死亡而对老船夫生出了些许嫌隙,总认为大佬的死亡和老船夫为人的弯弯曲曲脱不了干系。但是,当老船夫在风雨交加的夜晚突然逝,只留下涉世不深、无依无靠的翠翠时,他立刻放下之前的嫌隙,自觉主动地担当起整个丧事的操办。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杨马兵。杨马兵只因着年轻时对翠翠母亲的一丝好感,在翠翠爷爷突然过世,翠翠孤苦伶仃的情况下,揽下了照顾翠翠一切。杨马兵不仅在到渡船边小茅屋来照顾翠翠的日常起居生活,并且时刻关爱着翠翠的精神状况,小心地监视翠翠的行为,生怕她一时想不开跳崖悬梁,跟随祖父去。得空时,不时给翠翠讲故事,哄她玩,安慰这个幼小的遗孤。这就使得翠翠仿佛去了一个祖父,却新得了一个伯父这就是湘西的风土,边城的人情;这就是茶峒人们的善良和自觉自为的心。这份浓浓的人情、厚厚的美德足以让许许多多锱铢必较的人为之汗颜。这里没有尊卑之别,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没有勾心斗角、强取豪夺,有的只是心与心的交换、血与血的对流。人们淳朴善良本真自然的本性以及自觉自为的心,和清秀的山竹,明澈的河水交相辉映、有机融合,从而抒发了对美好人性、理想生存状态的向往之情。
由此,读者就能明白,作家沈从文为什么在作品《边城》的开头用如此完美细致的笔调来抒写茶峒的山山水水。我想,是想在作品的开头就展现给读者一个诗意性的背景,在行笔途中再增添几个和诗意性背景相映称的人物,从而组建一首清澈、美丽但又有些哀婉的田园牧歌。在这样一首美丽哀婉歌曲中,我们能感受到人与自然相互融合在一起的诗性内涵,也能感受到一种似乎为我们所陌生的自然、优美、健康的人性,那种如大自然本身一样凝重、而又本色真实的人生形式。因此,读这样的作品,我们获得的不只是文学艺术上美的享受,更是对广大读者心灵的滋养和疗补。
二《边城》的悲剧意味。
从抒情风格形态看,整部《边城》都潜隐着淡然而悠远的悲剧气息。实际上,沈从文小说的悲剧意识,表现为一种贯穿作品始终的悲悯情怀。其悲剧是自然而然化入叙述情节中,既不悲壮也不悲哀,仅仅在诗意化叙述中刻画几个简单的湘西人事,在这些人事上揉入了作家淡淡的悲悯感。
凡读过《边城》的读者,大都能体会到作品内淡然而悠远的悲剧内涵。在作品里,沈从文不惜浓墨重彩为广大读者刻画出了一幅明丽纯真而又动人的山水画卷。然而,在美丽画卷的外延下,却掩藏不住其散发出的淡淡凄凉感。这淡淡的悲凉感如影随行般蔓延渗透到作品的各个角落,从而奠定作品悲凉的情感基调。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作品通过哪些内容来抒发其悲剧气息并彰显其独特悲剧美的。
文本最先映入我们眼中的是茶峒中那一老一少相依为命的艰辛生活。老船夫70多岁,翠翠如今已十三四岁,十几年来都是靠着爷爷撑渡船的几斗米维持生计。这样的家庭组合,没有青壮劳动力,物质生活上自然就略逊一筹。因此,端午时节,船总顺顺且知道祖孙二人所过的日子,十分拮据,节日里自己不能包粽子,又送了许多三角粽。节日里都是如此寒碜,粽子都得劳他人接济,平日里过的啥样的日子那是可想而知的。不过物质上的贫瘠倒还是其次的,因着老船夫爷爷的硬气和,生活虽不富裕,倒还受乡邻们的尊重。最为关键的是家中没有主心骨,没有中坚力量,一切都得靠年老力衰的老船夫来强撑。如此一来,生活上稍微有点变数,这个家就面临摇摇欲坠的危险。我们知道,老船夫年纪大了,最为挂心的就是翠翠的婚事。他想在闭眼之前能为翠翠安排个舒心的去处,生怕她走了她那可怜母亲的旧路。因此,当大佬二佬同时爱上了翠翠时,老人本着自己微薄的能力,为着孙女的爱情幸福,三番五次千方百计试探着孙女的心事,极力尊重她的想法,不想让她受任何委屈。面对大佬直接的表白,爷爷表现的相当谨慎和模棱两可,这样的态度和沟通方式反而酿下了大错,致使大佬负气出走,命丧茨滩。爷爷也在船总顺顺一家的误会中内心积郁,最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溘然长逝。这个悲剧性事件里,没有谁对谁错,要怪得话只能怪那一老一少本身残缺的家庭组合,没有一个能利索主事的人。凭着善心做事的老人,因了自己对孙女的一丁点私心,反而给事情帮了倒忙。正如作家沈从文所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难免产生悲剧。故事中充满五月的斜风细雨,以及六月中夏雨欲来时闷人的热和闷热中的寂寞。
边城里,的笔触也涉及到了吊脚楼这一特殊阶层的生活状态。水手与畸形的婚恋关系不仅构成了沈从文观察湘西底层社会的一个独特视角,也构成沈从文湘西艺术世界中的苦难叙事。由于湘西地方上极端贫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下人不管如何勤劳,都很难把生活对付下去,这就使得女人以身体谋生的传统方式也在湘西地方上普遍存在。不过,沈从文笔下的不是惯常所见的那类风尘女子,她们出卖肉体不卖灵魂,她们有自身朴实简单的信仰。正如文中所讲的那样: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也永远那么浑厚,遇不相熟的主顾,做生意时得先交钱,数目弄清楚后,再关门撒野。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在她们身上,做人处事的美德并没有被她们悲惨的命运和卑贱的身份所玷污。因此,边城里,也是以诗化的艺术形象出现的。这些挣扎在地狱底层的们对生活怀着深切的爱,她们与水手相依为命,相互从对方身上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和生存下去的勇气。他们爱的大胆而有热烈,真诚而义气,完全袒露出生命的本真美,让众多表面上温情脉脉的爱情相形见拙。但是,这些诗化的形象并不能掩盖们残酷的现实状况:她们大都生活在狭小肮脏的吊脚楼或空船上,必须把出卖肉体当做一种赖以谋生的职业。沈从文把们屈辱人生和悲剧命运内化为一种异常沉重的苍凉,把们血泪斑斑却无处诉说的屈辱史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怎样的凄婉和哀伤!
与生的艰辛相比,《边城》中发生的一系列死亡事件就更具备悲剧内涵,也是作品中主要的悲剧。人自诞生以来,就伴随着死亡的到来。死,是人无法逃脱必须经历的一个课程。只不过,生命主体在生的过程中,贪恋着人生途中的各种美景,沉迷于人生中所谓的功成名就,压根就不去思考或者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死亡的问题。所以,当死亡突如其然来到你的身边时,你才会觉得格外震惊,格外手足无措,格外不可思议。其实,死和生一样,不过是人生的一种常态而已。只不过因为众生对生有太多的不舍才使得死更为哀痛。
文本囊括了三种死亡事件和三种死亡方式:有意外死亡的,如天保溺水;有自我灭亡的,比如翠翠父母;有自然死亡的,如翠翠爷爷。这三次死亡事件看起来是孤立的,实则具有深层的内在,有一种潜在的因果关系。这三次死亡事件总的根源在于翠翠父母的自杀身亡。翠翠的母亲和一个青年军官恋爱,但却不能自由结合,于是双双殉情而死。从表面上来看,他们的死并非不可避免,至少可以选择逃走。实际上却无法逃脱良心和的重负,因为一个不能不对军人的荣誉负责,一个不能不对自己的父亲有所交代。他们最终选择自杀来维护爱情的神圣。翠翠父母的死亡产生了悲剧性连锁反应。老船夫不得不承担起抚养孤雏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手续清楚。以避免自己女儿的悲剧在翠翠身上重演。正因为如此,老船夫在翠翠的婚事上就总是显得那么犹豫小心。如书中所言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老船夫的这种谨慎又导致大佬天保遇难,天保之死又使老船夫和顺顺之间产生误会,并导致二佬傩送出走,而这又影响到翠翠的婚事,最终使得老船夫在深重的内心隐忧中离开人世。这一连串的死亡事件中,谁都没有过错,然而却都是悲剧性结局。这种悲剧性结局里既抹上了浓重的人生空幻感和挽歌气氛,潜隐着哀婉凄凉的悲剧气息,同时又显现出人性美的光辉,从一个更深的层面展示出边城人们具有的良善生命形式。正如批评家李健吾所指出的,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推进, 而且自来带在人物气质里。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笼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原则:悲哀。
边城里,沈从文表面上是给读者们展现了一个绿水青山构成的桃花源式的自然环境,那里的人诚实、善良、仗义,那里的田园和谐宁静。而实际上,却是运用其寓含式的悲剧创作方法,使创作主体和客体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把这种距离的美感留给读者去揣摩玩味。无论是悲剧的创造者,还是悲剧的承受者都找不出具指的错,都被强制性地放到一种悲且美的艺术氛围之中衍生出悲剧的深层意蕴,揭示探讨人的生命价值意义之所在与人对生命强力的执着追求。
小说中的结尾这个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样的不确定性更增添了作品悠远的悲剧气息。
本文相关词条概念解析:
翠翠
翠翠,是沈从文中篇小说《边城》中的女主人公,是作者理想人生形式与理想爱情形式的寄托。她是一个天真无邪、自然善良、情窦初开的少女,是集真、善、美于一身的理想的艺术形象。她对船总顺顺的二儿子傩送一见钟情,却羞于表达。